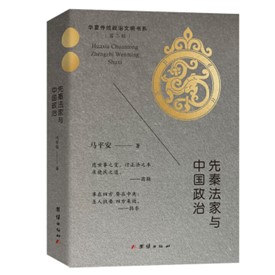法家虽然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但其思想之源却可以追溯得更早更远一些,甚至可以从善战重法的黄帝文化开始谈起。至于法家的直接文化来源,与儒家一样,实际上也是来自周王朝的王官之学。只不过不同的是,法家更注重汲取历代王朝的治国理政得失,更加注重实践层面的实际效果而已。法家的社会基础,是由非贵族的平民通过各种途径上升为土地所有者的新兴地主阶级或者新的官僚阶层组成的。他们所主张的“法治”是以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为形式的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他们所鼓吹的“法”体现的是与贵族集团相对立的新崛起的军功派的意志。这种意志正是由通过自己努力从基层崛起的新生利益集团的要求所决定的,即打破旧贵族对土地、政权和文化的垄断,用法律确保新兴利益集团的实际利益,保障他们进入社会上层,拥有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法家把贵族的“礼”说成是“私”的体现,而认定他们的“法”则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的正常体现。正是在这样的价值观念作用下,法家高举“以法治国”的大旗,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变法革新实践。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社会习俗等各个领域,涤荡旧时代的营垒,清扫古老的血缘纽带,构筑新的超血缘的以郡县制管僚制度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大一统的国家政治体系与新的统治秩序。 公元前 221 年大秦帝国建立。新成立的大秦帝国,按照法家理论的指导,彻底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郡守、县令皆由朝廷任命,中央政府可以随时对他们进行调动和罢黜。在中央政府,秦始皇也把在朝廷任职的官员按专门的官僚制度组织起来,设立“三公九卿”制度,形成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适合中央集权要求的行政机构和官吏制度。同时,推行“行同伦”“书同文”,推行文化统一政策;统一货币、度量衡;修驰道、通水路、去险阻、设邮传、大移民;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秦始皇推行的大一统政策是对春秋战国以来各国政治管理经验的一次全方位的提炼和升华。秦统一中国,不但标志着经过了漫长的酝酿和发展时期的大一统国家制度的正式诞生,更为重要的是奠定了“百代皆行秦政法”的基础,从此,大一统成为中国正统的国家形式和制度体系。大一统制度下的中央致府,通过庞大的官僚体系,对全国履行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管理功能,从而把传统中国社会结合成一个结构复杂、组织严密的统一整体,在大一统政府的统治下进行着有序的运动。这说明,从春秋到战国,法家的理论与实践阵地在不断扩大,最终成为中华初始帝国的治国理政模式。法家战胜各家,最终进入庙堂,应该说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然而,由于一项制度在开创时必然需要一定的探索过程才能成熟,大秦帝国在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军事、政治统一任务后,仅仅存留了15年便烟消云散了。一个无比强盛的泱泱帝国,何以二世而亡?这成了后世统治者和政治思想家们长期争论、众说纷纭的一个问题。经过探讨,他们一致认为,秦之所以亡国,就在于它贯彻了法家政治,严刑酷罚,不讲恩德,不重教化,使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一有风吹草动,反对派就会应者云集,使王朝最终土崩瓦解。实际上,这种简单的说法冤枉了法家。秦帝国的灭亡,其根源在于秦始皇死后接班人上面出现了问题,这恰恰说明秦始皇并没有将法家的统治术娴熟运用到位,而不能将这盆脏水泼洒到法家的身上。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秦帝国的夭亡,主要不是因为其政治制度、文化、政治理念、治国模式的方向性错误导致,而是最高统治者的个人私欲与行为不检点所引发。因此,汉承秦制是西汉统治者的一种明智的选择。通过继承前朝的一切优秀、合理的东西,汉王朝迅速迎来了它的盛世。 尽管刘邦是推翻了秦始皇的帝国而称帝,尽管从此之后汉代的史书、官牍把秦帝国描绘得一片黑暗,但是,汉帝国君臣却毫不犹豫地承袭了秦帝国的所有国家制度。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而言,秦帝国对中国政治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它创立了一套以大一统政治理念为标志的政治模式。这套政治模式包括政治观念、政治制度、法制体系以及与之相配套而成的社会经济体系。大秦帝国建立者的知识水平和理论水平明显高于起事于草莽布衣的汉帝国的创建者们。换句话说,秦始皇草创的政治制度和治国模式具有开辟性的特点及优势,继秦而起的任何新王朝都不可能再在一个短时间内创造出比之更加完备的国家制度。大秦帝国虽然因统治者施政不当而短命夭亡,但其创建的国家政体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不会随着秦帝国的消亡而消亡,而且以新的面孔继续决定与影响着继秦而后的历代新王朝的政治。历史发展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汉之法制,大抵因秦。”【1】根据云梦秦简提供的资料表明,许多原来以为是汉帝国创建的制度及其有关称谓,原来都是由前朝秦帝国那里传承下来的。“汉承秦制”,确凿无疑。一是汉帝国全盘接受了秦始皇创造的皇帝尊号及其相应的一整套皇帝制度与帝王观念。二是汉帝国承袭了秦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三是汉帝国承袭了秦帝国的郡县制度。四是汉帝国继承发展了秦帝国的官吏选任制度。五是汉帝国沿袭了秦帝国的监察制度。六是汉帝国还承袭了秦的赋税制度。七是汉帝国基本沿袭了秦帝国的礼仪制度。八是汉帝国对秦帝国的法律、德运、历法、风俗等也都加以承继。总的看来,汉帝国对秦帝国的继承是一种全方位的继承,也是一种发展性的继承。这种继承的特点表现在:秦开其端,汉总其成。秦帝国虽然夭亡,但其灵魂犹存,“祖龙虽死秦犹在,百代都行秦政法”。通过大汉帝国之身,大秦帝国以法家为蓝本草创的各种政治制度又变相地得以复活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大秦帝国就如一只涅槃的风凰,其灵魂在经过一场血与火的战争考验后又以汉帝国之肉身得以再生。 实际上,汉承秦制不是汉初统治者一时的心血来潮,它具有系统性与可操作性。大到政治制度、治国模式、疆域区划,小到许多具体的的习俗、礼仪、文字、度量衡等等,汉帝国统治者基本上都采取了全部的拿来主义。这表明,从秦至汉,整个政治制度及其社会文化体系是一种比较完整的继承关系,在一切主要方面都没有发生断裂。继汉之后,魏晋又承继汉制,以后,隋唐宋元明清各代一脉相承,“秦政”历经2000年而香火不断。由此,一个问题就必须作答:法家政治真的是随大秦帝国灭亡而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了吗?历史的答案是没有。 据《汉书·元帝纪》记载:“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这里就直接道出了汉代的治国方略——“霸王道杂之”。范文澜说:“武帝表面上尊崇儒家,实际上杀人很多,用的是法家的刑名之学。《公羊传》说:‘君亲无将,将而被诛。’意思是说,臣子对君父不能有弑逆的念头,如果有的话,就可以把他杀死。这个论点很合乎武帝随便杀人的意思。”【2】 事实上,从春秋战国直到汉武帝时代,以儒、法、道思想为主的各家思想经过长时期的“磨合”,最终“形成了礼法并用、德刑兼备、王霸结合的基本构架,这其中王霸结合是整体的概括,礼法并用、德刑兼备是其不同侧面的展开和延伸。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王与霸、礼与法、德与刑是双双对应的,相反相成,结构为一体,而王霸是涵盖礼法、德刑的。言王霸可以指礼法,也可以指德刑,当然可以指代自己;言礼法或德刑,在特定情况下,也可指代王霸。这一基本构架在儒法两家思想体系上,王道、礼治、德治和霸道、法治、刑罚又分别是两家思想体系主要支柱的借用。而这种‘借用’又不是绝对一一对应的,虽不能说王、礼、德就绝对是儒家的,而霸、法、刑又确乎可以说完全是法家的。也就是说,儒家在思路上是两点论,法家是一点论。儒家的两点论无法家一点论的配合就落不到实处,是悬空的;法家的一点论任其发展又走向极端,造成很多弊端,它必须回过头去受儒家的制约。这样,一虚一实,一高一下,便可以构成立体网状,相反相成、相互对立、相维相济的结构体”。【3】自汉统治者整合以后,儒法两家互补政治文化模式,就一直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理政的主要模式,为造就雄浑、质朴、开放、刚柔相济的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奠定了中华民族此后2000年历朝历代治国理政模式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家已经是不朽之身了。 注释: 【1】《容斋随笔》卷9。 【2】《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310页。 【3】 韩星著:《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245 页。 (马平安,历史学博士、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摘自马平安《先秦法家与中国政治》,该书由团结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