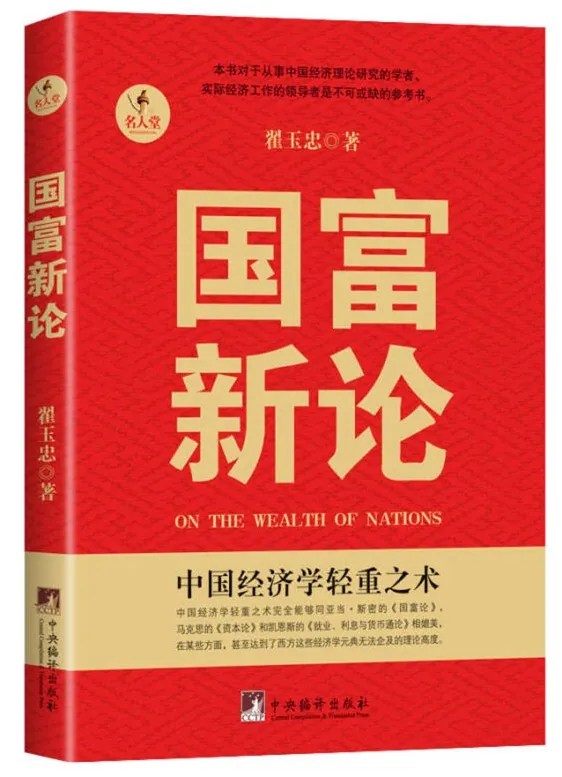物极必反,这条宇宙发展的普遍规律不仅适用于一般事物,也适用于一种理论。 经春秋战国,当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之术理论上逐步成熟起来,实践上创造了西汉富强甲天下的奇迹时,她亦开始走向衰落——其衰落的始点是公元前81年西汉政府召集的盐铁会议。 可以说,在过去五千年里,没有一个事件像公元前81年西汉政府召集的盐铁会议一样对人类历史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它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一场宫庭斗争,它改变了中华文明的颜色;它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中国,催生了目前仍占西方主导地位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今天,世界范围内的左、右政治之争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盐铁会议上引起激烈争论的议题。 站在21世纪的晨光中,让我们一起回顾两千多年前的这次会议!目的在于返本开新,为人类寻找可替代道路,提供有益的,甚至是核心的思想资源。 一、历史定格于公元前81年 公元前81年(西汉昭帝刘弗陵始元六年),农历二月一天的大早,世界上最大城市长安(比当时的罗马城大3倍),天气还很冷。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他们各自的属员丞相史和御史,还有去年刚刚选举出来的60余位贤良、文学匆匆赶往大汉王庭,参加13岁的汉昭帝下诏召集的经济会议,议题是讨论是否结束盐、铁、酒类由国家专卖给事宜。班固《汉书· 昭帝纪》记载说:“二月,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 没想到,一场本来议题简单的经济会议很快演化为一场国家大政方针的交锋,在一次次激烈漫长的讨论中,议题延伸到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经济到政治、从法律到外交,从历史观到生活方式…… 大约十年后,汉宣帝时的庐江太守丞桓宽根据会议资料及参加此次会议的同乡好友朱子伯的追述,这位研习《公羊春秋》的儒者出于“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的宏愿,推衍增广,整理出了洋洋数万言的《盐铁论》,使我们有幸如临其境地了解这场会议的真相。后世又称《盐铁论》为《贞山子》或《桓宽盐铁论》。 桓宽,生平不详,据《汉书》所记,他字次公,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人。博通典籍,善于文章,平生研习《公羊春秋》,与同乡朱子伯交游深厚,后被荐为郎官。汉宣帝时,官至庐江太守丞。 或许桓宽本人也没有想到他铸就了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以后,以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之术为代表的中华原生文明形态逐步落下了帷幕,儒家倡导的小农主义的自由政治经济思想逐步垄断中国人的全部生活——他们激进地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甚至发展到反对“言利”。《盐铁论》的每一章节都显示出两种治世理念的针锋相对:在“分水岭”的一边,是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官方正统思想力量集团,另一边,是正在兴起的民间儒生思想力量集团。难怪东汉王充在《论衡·案书篇》中称本书是“两刃相割,利害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 公元前81年的时候,近乎没有人相信那些儒生将来会成为中国政治的主导力量。桑弘羊甚至说他们“固未可与论治也”。(《盐铁论·相刺第二十》)儒生们反对盐铁专卖,但盐铁会议之后盐铁官营的政策并没有丝毫改变,只是五个月后才有限度地取消了酒类专卖,撤销了主管酒类专卖的官员,改为实行价格控制,限酒价每升四钱。 盐铁会议上儒生的所有主张几乎都没有成为现实政策,这时他们还只是一只只漂亮的蝴蝶,在长期以黄老之学治国的西汉王庭中拍了几下翅膀。但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的确掀起了一场席卷世界历史的急风骤雨! 那么盐铁会议是如何实现“历史的蝴蝶效应”的呢?让我们从头说起。 二、盐铁会议的缘起 公元前87年,一代天娇汉武帝驾崩。 武帝一生南征北战,开疆拓土。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后,匈奴从此无力大举南下,出现了“匈奴远遁,漠北无王庭”(《汉书·匈奴传》的局面。至少在表面上,外部的威胁基本上消失了,这在现实层面增加了儒者奢谈以德治国的可能性。因为从孔子到孟子,再到汉初诸儒,在外部强大的威胁之下,他们的主张显得过于迂腐。 这不是说,匈奴的威胁已经不存在,机动性强的匈奴人寇边之事仍时有发生。汉昭帝即位的第一年冬天,匈奴就入侵朔方郡,杀戮吏民,掠夺财物。汉朝廷不得不发兵进驻西河郡,并命左将军上官桀巡查北部边疆。据《汉书·昭帝纪》载:“冬,匈奴入朔方,杀略吏民。发军屯西河,左将军桀行北边。” 从汉朝内部看,当时儒生尽管还没有深入文官队伍,但其社会影响力已经极为强大,如董仲舒的思想成为一时显学——通过私学教育手段影响社会进而影响政治轴心,是儒家最后实现独尊地位的历史路径。 在盐铁会议上,主要代表儒家思想的贤良文学显然深受董仲舒这位一代儒宗的影响。王利器先生在《盐铁论译注》序中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写道:“参加这次会议的60 多个贤良、文学,他们都是‘祖述仲尼’的儒生,除了心不离周公,口不离孔、孟之外,还宣扬当时‘推明孔氏’的董仲舒的学术思想。董仲舒是向汉武帝建议要‘盐、铁皆归于民’的始作俑者。他攻击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他在对策时,宣扬‘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儒家说教,反对‘与民争利’,认为‘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他之所谓民,并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指的豪门贵族和富商大贾。本书《禁耕篇》所谓:‘夫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复古篇》所谓:‘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正好说明董仲舒扮演的‘为民请命’这出剧是怎么回事了。”[1] 不仅民间儒家思想盛行,汉昭帝本人似乎已不再重视黄老,从一年前(公元前82年)他在下令察举盐铁会议上这60 多个贤良、文学的诏书中我们看到,这位少年天子所列举的自己所读之书,都是儒家经典,包括《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无一西汉初年流行的黄老法家作品。《汉书·昭帝纪》收录了这一诏书:“朕以眇身获保宗庙,战战栗栗,夙兴夜寐,修古帝王之事,诵《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 请读者一定注意,从诏书中我们看到,参加这次会议的贤良都是由三辅、太常选拔出来的。当时,太常的职责是掌治帝陵,《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太常……诸陵县皆属焉。”而其地“皆徒天下豪富民以充实之”。所以这些贤良可以肯定出身于豪门,显然是富民的理想代言人。 由此我们看到,公元前81年,汉王朝从上到下,代表富商大贾的儒家思想已经侵入整个社会机体。当外部条件适合的时候,这一思潮终将以某种形式爆发出来——盐铁会议的召开变成儒家思想爆发的导火索,点燃它的是当时手握朝庭权柄的霍光。 三、盐铁会议的始作俑者霍光 参加盐铁会议的权臣有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但幕后的始作俑者却是当朝的主政大臣霍光。 霍光,字子孟,霍去病的异母兄弟。正是年轻有为的一代名将霍去病将霍光带入了宫庭。他没文化、没功绩,只有忠诚。靠小心谨慎得以在权力的中心步步高升,最后竟成为汉武帝的五位托孤大臣之一(当时昭帝年仅八岁),其他几位分别是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 这些人中,丞相车千秋是个明哲保身的专家,同霍光一样,没有什么才能,连匈奴人都称他“妄一男子”。昭帝即位后,他每每讨论政事总是一言不发,将权力让给霍光,霍光也乐此不疲,投挑报李,总是寻机嘉奖他。《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载:“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听政,政事一决大将军光。千秋居丞相位,谨厚有重德。每公卿朝会,光谓千秋曰:‘始与君侯俱受先帝遗诏,今光治内,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负天下。’千秋曰:‘唯将军留意,即天下幸甚。’终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应,数褒赏丞相。” 在关系国家政治方向的盐铁会议上,车千秋照样几乎一言不发,结果盐铁会议成为桑弘羊同儒生集团的单打独斗。连《盐铁论》的作者桓宽都指责说:“车千秋丞相处于周公、吕望的地位,在会议中像车轴一样处在中间,闭口不言,保全自身,他呀!他呀!”(原文:车丞相即周、吕之列,当轴处中,括囊不言。彼哉!彼哉!) 车骑将军金日磾在昭帝上台后不久(公元前86年)就死了。盐铁会议会第二年,左将军上官桀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在宫庭斗争中一起被诛杀,最后霍光得以独揽大权。 据《汉书》,最早向霍光提出召开盐铁会议的是霍光亲信的属吏杜延年。杜延年出生于法律世家,却不赞成重其轻者的刑事政策,他的两个哥及其父杜周办案以严闻名,其独宽厚。杜延年主张召开盐铁会议的理由是汉武帝年间战争费用太高,要回归汉初的政治,所谓“孝文明政”,这显然是个幌子,因为盐铁会议上的民间力量没有一个治黄老的学者,倒是请来一大批儒生。《汉书·杜周传》载:“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明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光纳其言,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皆自延年发之。” 此后,汉代儒生常常通过抬高文帝的办法贬低武帝的治国政策。问题是汉文帝施行的是黄老治国思想,而不是儒家治国,二者有天壤之别。盐铁会议召开的真实目的是以儒家治国理念代替黄老治国理念,所以桓宽干脆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舒六艺之风,论太平之原”(《盐铁论·杂论第六十》)。 四、盐铁会议令人惊异的“蝴蝶效应” 细心的学者早就发现,盐铁会议的影响在汉代就显示了出来。不仅仅是有限度的开放酒类专卖这一项。比如,盐铁会议上遭儒生猛烈抨击的均输制度,此后很少有人提及,元帝时罢除被儒者反对的盐铁官和常平仓。均输之制到西汉末年已渐废弛,东汉初年正式省罢。盐铁会议召开160多年后,章帝元和年间(公元84~86)尚书张林建议恢复,因遭到自己副手(尚书仆射)朱晖的坚决反对而未能施行。朱晖反对的理由仍是被长期误读的“不与民争利”,核心是主张放任主义的自由经济理论。他说:“按照先王礼制,天子不说有无,诸侯不说多少,享受俸禄食邑之家不同百姓争夺利益。如今均输之法同贩卖没有区别,盐的利益归官府,那么下边的百姓就会贫穷怨恨,用布丝绸作为租赋,那么吏就会邪恶偷盗,实在不是圣明之主所应当施行的。”(《后汉书·朱乐何列传》原文:王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禄食之家不与百姓争利。今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盐利归官,则下人穷怨,布帛为租,则吏多奸盗,诚非明主所当宜行。) 儒家主张的放任的、小农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影响社会阶层平衡的兼并之徒兴起。西汉成、哀年间已经出现了罗裒这样往来京师、巴蜀间,“訾至巨万”的大盐商。至东汉,儒学士族门阀集团崛起,儒生对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成为一种常态,并延续达两千年之久。 如果说亚当·斯密,这位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直接受到盐铁会议的影响,可能大多数人会以为是天方夜谭,但从马克思到熊彼特,世界上却很少有人能够否定,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来自法国重农学派,而重农学派则直接受到了儒家经济思想的影响。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写道:“尽管盎格鲁-撒克逊人偏狭地认为亚当·斯密是第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却又认为斯密的背后是法国的‘重农主义者’魁奈,而关键的是,在魁奈的背后是中国,第一个批判重商主义思想的欧洲人,是魁奈,而不是亚当·斯密。”[2] 在十八世纪欧洲知识界,中国在他们心中的地位一如今天美国在许多中国学者心中的地位。在这种历史氛围中,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受中国的影响当是自然而然的。具体路径是:中国儒家——法国重农学派——英国亚当·斯密。 1746年亚当·斯密陪巴克勒公爵到法国旅行时结识了重农学派的核心人物杜尔哥和魁奈,亚当·斯密的传世名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实际上是仿效杜尔哥的著作《关于财富的形式和分配的考察》而作;他本想将《国富论》献给魁奈,可惜该书出版时,魁奈已去世。 十八世纪法国重农主义代表人物魁奈受中国儒家经济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专门写了《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看作榜样。1946年,美国的Lewis Maverick教授在该书的英译本绪论中谈到自己的研究路径时这样写道:“我在阅读中国古代哲学家孟子的著作时,发现他的论述与18世纪法国重农学派的论述非常相似。于是我萌发了一个想法,决心去探索中国人通过哪些途径影响了这些法国人。”[3] 事实上,19世纪末就有人注意到重农学派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1896年,亨利·希格斯以鄙视的态度,在他的《重农学派》一书中提到重农学派受到中国“特别强烈的影响”。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热潮在二十世纪才真正开始。Lewis Maverick教授1938年发表在美国《经济学史》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明确指出:在20世纪经济学家从法国重农学派那里继承的遗产中,仍保留有来自东方的沉淀物;因些,西方经济学家不应把研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思想看作是与西方文明毫不相干的外来物,而应认识到它们对于西方思想的发展作出了直接贡献。[4] 约翰·霍布森进一步指出,魁奈思想当中有很多概念受惠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无为”概念译成法文的laissez-faire(自由放任主义)。[5] 历史简直是阴差阳错!因为在中国古典政治经济思想中,“无为”不是“不为”,其本意是“为无为”,就是在适当时机干预(经济)事件的进程,不是自由放任,政府什么都不作——是儒家思想和实践让西方明以后来华的传教士误读了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西方经济学主流由此走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不归路! 从董仲舒及盐铁会议时代的儒家,从儒化的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到法国重农学派,再到英国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最终形成,盐铁会议这只蝴蝶的影响所及至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贯穿其中的思想脉络清楚可见: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它支撑起了庞大而保守的儒家文官集团;在西方,它为资产阶级垄断世俗权力铺平了道路。 从东方到西方,历史是怎样的奇妙啊!两千多年前一小撮儒生反对盐铁专卖,到今天主张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汹涌澎湃——二者本是同根生! 注释: [1]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上,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9页。 [2]约翰·霍布森著/孙建党译:《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页。 [3]弗朗斯瓦•魁奈著/谈敏译:《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英译本绪论”,第1页。 [4]弗朗斯瓦•魁奈著/谈敏译:《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英译本绪论”,第4~5页。 [5]弗朗斯瓦•魁奈著/谈敏译:《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英译本绪论”,第176页。 (本文摘自翟玉忠《国富新论:中国经济学轻重之术》,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