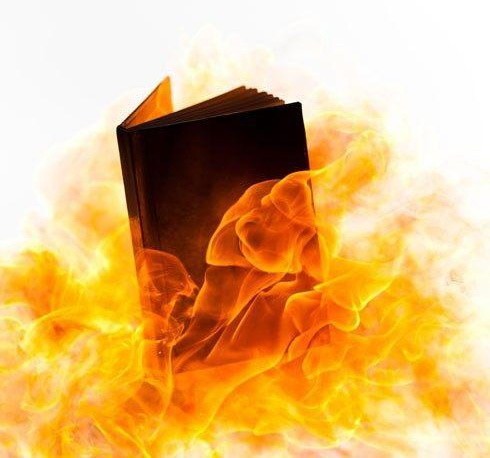过去两千年,中国古典学术的分类只有两大类型。一是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所创的七略图书分类法,它按学术内容和社会功用将当时的图书分为六大类,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另加辑略总括学术源流,合称“七略”。二是西晋荀勖(xù)开创的四部分类法,即后世的经、史、子、集分类。 二者相比较,七略分类法更能反映中国文化固有的学术体系,而四部分类法则更多迁就了史书和文集发展的现实。比如在七略中,史书本来属于六艺的“春秋类”,一经单纯分出,史学中蕴含的春秋大义则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了。但史书越来越多,从六艺中分出也有其必然性。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锦民先生写道:“《七略》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是以学术分类统领图书分类,某一类书恰好就是某一专门之学。四部分类法则更多迁就图书增多的现实,以方便著录图书为原则,于是打乱了原有的学术格局,书与学二者不再相互吻合。不过,学术的发展和文献的发展都是有历史性的,二者的相合也是历史性的,并非一成不变的。”【1】 唐初编纂《隋书·经籍志》时,就是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之后它成为官修目录和史志目录普遍采用的分类法。以至于后人谈到中国文化,也以经、史、子、集概括。 过去百年来,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被西方学术体系重新定义,并以此为原则“整理国故”。无论学者们出于有意还是无意,结果经、史、子、集的本来面目被遮蔽了,其内容和社会功能被全面消解——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焚书运动”之一,只不过所用之“火”乃一种外来的、异质的学术体系。也因此,这种“焚书运动”也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 那么近代以来学者是如何尘封以经、史、子、集为主体的中国古典学术的呢?兹分述如下—— 1.经书表达了中华文明的根本价值观念 自胡适将清代大儒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演绎为“六经皆史料”,经学就从中华民族大经大法的崇高地位跌落,成为普通的史料。比如《尚书》成了“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春秋》成了“中国春秋时期的编年体史书,记录了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鲁国的重要史实”;《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经书的确源于三代政治教化史实,但这是模式化、义理化的史实,是用以表达中华文明根本价值观念的,所谓“因事以寓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总序》)。其意义已经超越一般的史料。如果将经学还原为史料,就如同将一个活生生的人还原为一团碳水化合物——这是残害生命,是愚蠢的,也是荒唐的。 也因此,经学义理被野蛮剥离。这样做,我们不仅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特色和中国模式,甚至基本的社会价值都成了中西价值观念的随意堆积——这样的社会价值观念一般人很难记住,又怎能起到教化人心的作用呢? 2.史书编写不能脱离《春秋》大义 人们通常认为,中国史学也和中国历史一样源远流长。事实上,史学作为独立的分类出现很晚,《七略》中根本就没有史部,史部属于经学中的春秋类,且地位高于诸子百家和数术方技。 司马迁写《史记》,其志向也是续写《春秋》。尽管他曾谦虚地对上大夫壶遂说,自己所记的旧事,只不过整理了世代所传,并非所谓创作,不能拿它与《春秋》相比;但司马迁续写《春秋》目的显而易见。他在谈到自己作太史令,继承父亲遗志整理国家珍藏的史料时说,我的父亲曾经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五百年,有能宣扬盛世功德,辨正《易传》,接续《春秋》,遵奉《诗》《书》《礼》《乐》精义的人吗?”他的用意就在于此吧!我又怎敢推辞呢!《史记·太史公自序》:“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反过来说,史学即经。所以自司马迁之后,传统史家写史,皆以大一统的《春秋》大义为作史原则,以代表大一统政治的皇权为中心。然而自1902年梁启超称:“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2】将二十四史诬称为二十四姓之家谱,中国史学传统笔法尽失。引入西方五花八门的史学思想,几乎无关史学服务于国家大一统这一根本宗旨。 近代西化的史家,让我们拥有了更多史学的知识,却使我们失去了史学的灵魂!中国经史之学的灵魂是治国理政,而西方史学脱离治国理政之核心,还将史学碎片化,乃至庸俗化、娱乐化。所以说引进西学可以说是拣了西方史学的芝麻,丢了中国史学的西瓜。 本来,我们应该为前朝著史,但长期以来学人在如何写《清史》的问题上不能统一思想,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春秋》大一统真义已知之甚少。 3.诸子百家从不同维度论治国理政之法 西方现代性叙事的底层逻辑是欧洲中心论,它以西方的一切为现代、优秀、先进,其他文明的一切则为传统、低劣、落后。其全部意义最多也只是历史价值。所以,从胡适开始,中国古典学术体系就已经被史学化了。至于诸子百家的思想,由于表面上类似于西方哲学,所以就被纳入了哲学史范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不幸的是,诸子百家的学术理路与西方哲学观念大相径庭。以西方哲学理念整理诸子百家,必然会方凿圆枘,驴唇不对马嘴。最显著的,中国人没有西方那种将现象与本质区分开来的思维方式,先哲重视现象,常常通过模式化和理想化的典型现象阐发正确的做事方法——道;西方哲学不是这样,它重视变动不居现象背后不变、普遍的本质形式,西方哲学关键是要求真,而非致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方朝晖教授写道:“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C.Graham)曾指出,中国文化中没有西方人那种将现象与本质区分开来的思维方式(张东荪、张岱年也早就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中国人更相信‘正名’。葛瑞汉的说法也许引起国人不满,以为是偏见,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是经常说透过现象看本质么?中国人讲的道、天理难道不是本质么?其实葛瑞汉指的是中国人以感官经验为真,以感性事物为实,故无柏拉图、洛克那样以感官属性为幻,在感官经验背后寻找本体的传统。至于我们经常说的透过现象看本质,指的是如何更好地理解经验发生的规律从而更好地适应或利用它,并非在感官经验现象背后去寻找可以客观验证和理性证明的本质。”【3】 由于中国没有西式哲学,所以冯友兰干脆抛弃了西方以求真为目的的宗旨,而采用了西方泛化的哲学定义,认为哲学定义是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事实上西方诸多学者是对的,他们注意到中国并没有“哲学”。 也只有承认诸子百家不是西式哲学,我们才能认识诸子百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一语道破了诸子百家的本质:“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诸子百家从政治教化等不同维度论治国理政之法,它们相辅相成、相须为用。 《汉书·艺文志》总论诸子百家说,现在各家都推崇自己的长处。深究事物的始末,探明其要旨,即使有些弊端,综合他们的要领,也都是《六经》的支和流。假使诸子遇到明王圣主,得到他平正的对待,这些人就都能成为治理天下的大才。如果能学习六经,再深入这九家的言论,扬长避短,就可以通晓治理天下的种种方略了。《汉书·艺文志》:“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不幸的是,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后,研经之儒大兴,连荀子、孟子那样的先秦儒家都衰落了,更别说其他诸子百家——《孟子》受到重视是在宋以后。王锦民先生指出:“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可以清晰地看出诸子的渐衰,汉魏六朝诸子不及先秦诸子远甚。除了儒道两家,后续的创造性著作屈指可数,如名、墨诸家更是成了绝学。”【4】 在诸多学者将儒学等同于中国文化本身的21世纪,我们摆脱“独尊儒术”桎梏,复兴诸子百家,恢复以经学和子学为轴心的中华治道,任务仍十分艰巨。 4.集部承担着文以载道、人文化成的社会职能 集部源头可以上溯至《诗经》,其目的在于社会教化、修齐治平。所以“诗三百”先列各国之风。《诗大序》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作者的意思是说,风的意思就是讽喻、教化,用讽喻来感化人们、教化人们。诗是人们用来表达志向的,蕴藏在内心就是志向,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所以匡正政治得失,感动天地鬼神,没有比诗更接近于实现这个目标。前世的君王用诗歌来规范夫妻关系,养成孝敬行为,敦厚纲常伦理,美化教育风气,改变不良风俗。 西汉时,扬雄等学者就曾批判缺乏讽刺劝诫作用的“纯文学”作品。《汉书·艺文志》总论诗赋时指出,大儒荀子和楚国的大臣屈原,因为远离谗言、忧心国家,都写下作品来委婉劝谏,他们的作品饱含着古诗那样同情他人、忧国忧民的情感。后来宋玉、唐勒,汉朝兴起后的枚乘、司马相如,再往后到扬雄(扬子云),都争着创作华丽铺陈、气势宏大的辞赋,却丢掉了其中委婉劝谏的深意。所以扬雄后悔了,他曾写道:“诗人写的赋既华丽又有原则(能起到劝谏作用),而辞赋家写的赋文辞华丽却流于浮夸(过于追求形式而失去实质)。如果孔子的弟子也写赋的话,那么贾谊和司马相如的水平就能登堂入室了。如果不用赋来发挥劝谏作用,那写赋还有什么用呢!”“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从根本上说,中华文脉与道脉是合二为一的,文风与政风也紧密相连。近代以西方文学理论范式生硬切割集部,结果只能是学术理论的无限混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郭齐勇教授评论道:“就文体而言,由于西方只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几种,那么汉赋的归类就成了令中国现代文学家们头痛的难题——它是诗歌呢?还是小说?按西方标准,诏、策、令、教、表、启、书、檄等等,均不能属于文学的范围,收录这些文体的《昭明文选》不能算做纯文学总集,讨论这些文体的《文心雕龙》也不能算做纯文学理论著作。以西方关于小说‘有一定长度的虚构的故事’的定义,中国正统史志著录的小说都不合标准,以致于迄今我们还拿不出一份大家公认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以西方所谓‘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方法来框中国文学的方法,够用吗?我们的比、兴等象征手法算什么呢?”【5】 是我们为经史子集正名的时候了!如果继续走过去一百多年“输入学理、整理国故”“以西释中”的老路,我们不仅不能保存国故、再造新文明,反而会解构国故、毁灭中华魂!这是一种文化自残,文明自杀! ——猛醒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
注释: 【1】王锦民:《古典目录与国学源流》,中华书局于2012年版,第114页。 【2】梁启超:《中国之旧史学》,载1902年2月8日《新民丛报》。 【3】方朝晖:《重思中国传统学问中的本体问题》,载2023年2月8日《中华读书报》。 【4】王锦民:《古典目录与国学源流》,中华书局于2012年版,第348页。 【5】郭齐勇:《出土简帛与经学诠释的范式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