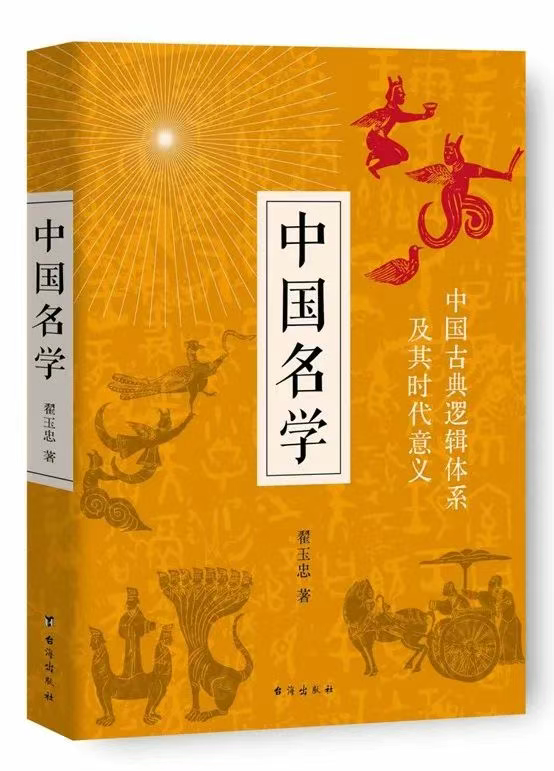所谓“三物”,即形成推理,立辞的三条规则:故、理、类。 名学“立辞三物”出自《墨子·大取篇》,上面引《语经》言曰:“三物必具,然后足以生。(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今人非道无所行,唯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 何谓“语经”。在古代汉语中,语和言是有区别的。汉人注经,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发端为言,答难曰语;言己事为言,为人说为语。所以“语经”可以理解为论辩的基本原则。当代治墨大家谭戒甫(1887-1974年)也说:“此言立辞必具三物,三物具足,不可缺减;由是辞足以生,而辩论庶几无过矣。”【1】 伍非百先生释“立辞三物”云:“所谓三物者,‘故’‘理’‘类’也。无‘故’,则其说无所根据;无‘理’,则其说无所衍绎;无‘类’,则其说无所推行。故曰‘三物必具,然后足以生。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故,即《墨经》‘大故’‘小故’之故(故分两类,《墨子·经说上》云:“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不必然……大故,有之必然。”——笔者注);与今言‘前提’、言‘因’者近是。理,条理、分理也;有分析与综合之意。类,谓同异之类也;与今言‘喻’、言‘例’、言‘比类推理’者近是。《荀子·非二十二子篇》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即举‘故’‘理’二物以评立说之价值也。本篇云‘其类在某’即举‘类’以行说也。”【2】 邢兆良先生在《墨子评传》中与西方逻辑学对比,解释“立辞三物”十分详尽。对于“故”,他认为墨子所说的思维过程并不是三段论式的,“故“也不等于三段论推理的小前提,因为在《墨经》中“故”并非结论成立的部分理由和论据,“墨子所说的故是结论成立的充足理由,它是结论成立的全部前提的总和,是立辞的全部根据,而不是全部理由、根据、前提中的某一部分。”【3】邢先生认为“故”有两重涵义,“首先,它指的是客观事物的所以然之故,是事物、现象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或条件,所谓‘故,所得而后成也’。其次,它是指立辞的理由和根据。一个论题必须有充分的论据才能成立,一个推理过程的前提和结论必须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这种逻辑关系是前提所蕴涵、规定的,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过程是蕴涵关系的展开。所以说,辞以故生。”【4】 对于“理”,邢先生认为它也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客观事物、现象发生和存在的自身根据。二是指在逻辑推理、论证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法则或规则。同时,“墨子说的理不是指三段论推理过程的大前提,而是指整个推理过程中所应遵循的逻辑规则。”【5】理,即是道,即是法,即是仪,所以《墨子·非命上》提出:“(言)必立仪,言而无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 墨子认为,言说没有准则,就好像在旋转的陶轮之上放立测量时间的仪器,这样不可能弄明白是非利害。接着墨子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三表法以历史经验为本,以现实情况为原,以社会实效为用,将社会科学建立在了可参验的基础之上——这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对于“类”,邢先生认为它是《墨子》逻辑体系的核心范畴,“类范畴为概念的确立,定义的划分及其相互联系提供了一个框架”,【6】 “类为判断的形式及不同判断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提供了一个判别基础,人们只有根据这类事物和他类事物之间的同和异,才能作出明确的判断”,【7】 “类为推理能得以合于逻辑地进行提供了基本前提。如墨子所说的:‘推类之难,说在类之大小。’‘异类不比,说在量。’”【8】 墨子特别注重“察类”,比如他反对不合道义的侵略战争“攻”,但并不反对合于道义的正义战争“诛”,在墨子看来,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墨子·非攻下》记载了那些好战之君对墨子的非议:你认为攻战为不义,难道不是有利的事情吗?从前大禹征讨有苗氏,汤讨伐桀,周武王讨伐纣,这些人都立为圣王,这是什么缘故呢?墨子回答说,这些人“未察吾言之类”,上述圣王的讨伐不叫作“攻”,而叫作“诛”。文中说:“今遝(通“逮”——笔者注)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为不义 ,非利物与?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 “立辞三物”重故、重理、重类,有效防止了西方逻辑体系常常引发的玄辩陷阱。《老子·第三十二章》云:“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西方建立在抽象定义和假设公理之上的逻辑体系常常“不知止”,这是西方学术容易陷入经院化的重要原因。在此意义上,名学正好补西方逻辑学之不足。 (选自《中国名学:中国古典逻辑体系及其时代意义》,该书可在京东、当当上买到;支持我们,欲购作者签名版请加微信:zhai20050718) 注释: 【1】谭戒甫:《墨辩发微》,中华书局,2005年,第450页。 【2】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38—439页。 【3】邢兆良:《墨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4页。 【4】邢兆良:《墨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3—334页。 【5】邢兆良:《墨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5页。 【6】邢兆良:《墨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7页。 【7】邢兆良:《墨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8页。 【8】邢兆良:《墨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