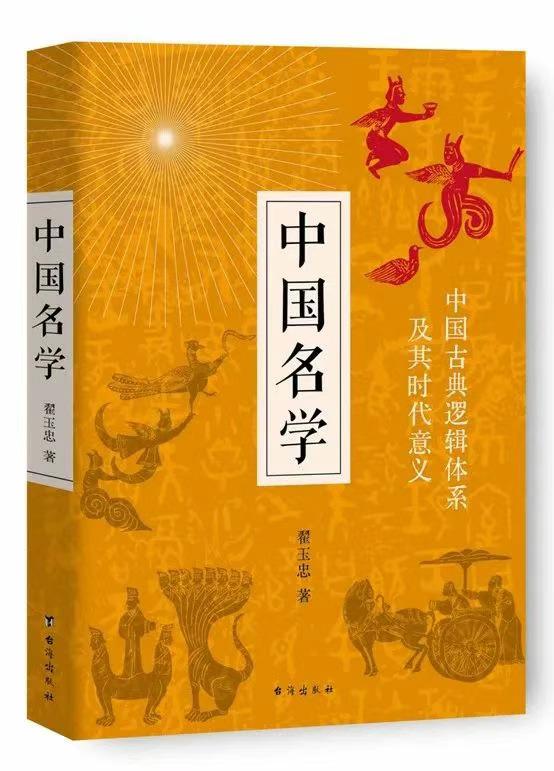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体系,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印度因明学逻辑体系和中国古典逻辑名学,因为前两者与宗教的密切关系,至今仍然流传不绝,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体系,经过数理化,已成为21世纪人工智能时代的重要基石。 三大逻辑体系中,只有名学早在魏晋时代已渐成绝学。清末民初,受西方逻辑体系的强烈冲击,中国学人欲复兴名学,受“以西释中”,以西方学术理论整理中国本土知识思潮的影响,名学的复兴历经百般曲折。导致名学的本来面目及其推理方法长期以来得不到正确的认识。 1924年2月1日,陈独秀在《前锋》第3号上发表了《国学》一文,他评论胡适(字适之)、章士钊(字行严)研究名学的误区时就曾指出说:“如适之、行严辛辛苦苦的研究墨经与名学,所得仍为西洋的逻辑所有,真是何苦!”【1】 因为中国名学本与西方逻辑学学术品质迥异,我们不能生搬硬套西方逻辑学概念研究名学。 “百家务为治”,作为诸子百家之一的名家同样具有深刻的现实关怀。名学不仅是一种逻辑体系,更是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这是它与西方逻辑学、印度因明学大相径庭之处。 名分是名学的重要概念,指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以及相应的社会责任,在伦理和政治生活中将名位与职责相参验,可以直接用于社会治理,这使名学成为儒家名教之学和法家名法之学的基础,而西方逻辑学显然缺乏这样实用性的社会治理功能。 《战国策·韩策二》很能说明名学的社会功用。据说史疾为韩国出使楚国,楚王问他在研究哪方面的什么学问,史疾回答自己学列御寇传授的正名之学。 楚王感到不解,问史疾:“正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吗?”史疾说:“当然可以。” 楚王又问:“楚国盗贼很多,用它可以防范盗贼吗?”回答说:“当然可以。” 楚王接着问:“如何用正名来防盗?”正在这时,有只喜鹊飞来停在屋顶上,史疾问楚王:“请问楚人把这种鸟叫什么?” 楚王说:“叫喜鹊。”史疾又问:“叫它乌鸦行吗?” 楚王回答说:“当然不行。” 史疾就说:“现在大王的国家设立柱国、令尹、司马、典令等官职,任命官吏时,一定要求他们廉洁奉公,胜任其职。现在盗贼公然横行却不能加以禁止,就因为各个官员不能胜任其职,这就叫做‘乌鸦不称其为乌鸦,喜鹊不称其为喜鹊啊!’”【2】 另外,通过中国名学研究,我们还能充分认为西方逻辑学的局限性。西方学术建立在对现实的抽象定义和系列假设基础之上,一旦沿着逻辑链条推演下去,常常发生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所谓的“文辩辞胜而反事之情”的现象。就是道理上行得通,却与现实不着边际——“理胜情”已经成为现代西方人文学术的痼疾,这在西方经济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现代西方经济学通过数学工具的普遍应用高度数理化,逻辑形式上更加完美,但它除了为华尔街贪婪的银行家提供骗人的金融产品之外,根本不能拿出应对现实经济多重危机的方案,这种现象在西方经济学界内部也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中国人民大学贾根良教授接受《海派经济学》记者采访,谈到过去十多年风起云涌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 时提到了经济学回归现实,回归以问题为中心的新方向——要知道,“以问题为中心”正是《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中国学术范式的根本特点之一。贾教授指出: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西方国家控制的教学科研是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和数学工具为中心的,即根据工具选择所要考虑的经济现实类型,其结果是大量的经济现实被从教学科研中排除掉了,甚至是数学工具的教学和运用也与现实问题毫不相关,他们教授和分析的对象是一个虚构的世界。这实际是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的体现,是以教条为中心的。针对这种现状,法国经济学学生在引发改革运动的请愿书中大声疾呼:要摆脱虚构的世界,反对滥用数学。在后续讨论中,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主张要彻底颠倒这种工具和经济现实之间的关系,以问题为中心,即不顾教条的束缚,根据所需分析的经济现实问题来选择或发展工具,工具运用本身不是目的,与分析的问题相关的工具才有存在价值。这种问题中心论,就是要求经济学的教育与科研要以当前重大的、紧要的经济问题(如收入分配、贫困、失业、社会排斥、生态危机、能源危机、国际金融体系等)为导向,以现实相关性为中心,使理论实质重于技巧、内容重于形式,真实压倒虚构,从而恢复和加强经济学的经验基础,将经济学带回现实。【3】 最后,中国名学(特别是“伪名”和“鄙名”理论)能够为本土学术提供牢靠的思维防火墙,同时建立起不同文明间交流的“学术海关”,避免出现逻辑概念的混乱,这一点是西方逻辑学难以胜任的。19世纪末,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和中国军事科技的一时落后,在救亡图存的现实压力面前,中国学人将目光转向了西方。过去一百年来,一波波囫囵吞枣地引入西学,导致了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名与实的严重混乱。具体表现为,我们引入的西方学术概念和理论(名)常常与现实格格不入,结果学人不仅不能很好的解释历史,也不能解释现实。 反映到名学研究领域,就是用西方逻辑学、语言学、符号学等解构名学。一些学者大谈 “墨家的形式逻辑”,“辞”就是西方逻辑学中的判断之类——这些人不理解,研究名学不能随意引入西方形式逻辑体系,否则就会引入诸多没有现实基础的“伪名”。“西学名立中学实从”,结果是中学的西学化,中国学术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的西学。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曹峰教授痛感名学研究“以西释中”之害,他写道: “名家”研究从一开始就有方向性错误,表现为不顾“名家”所生存的思想史环境,将西方逻辑学概念、框架、方法简单地移植过来,有削足适履之嫌。二十世纪后在西方学术背景下形成的先秦名学研究,只重视逻辑意义上的、知识论意义上的“名”,有时甚至曲解伦理意义上的,政治意义上的“名”,将其当知识论、逻辑学材料来使用。自从将“名”“辩”与西方逻辑学相比附后,只要谈到“名”,似乎就只能从逻辑的角度出发。【4】 名学就是名学,西方逻辑学就是西方逻辑学。我们在研究方法上一定要摆脱西方逻辑学的框架,按照名学内在的逻辑去研究,关键是弄清楚名学的一宗、二辞、三物、四法。 (选自《中国名学:中国古典逻辑体系及其时代意义》,该书可在京东、当当上买到;支持我们,欲购作者签名版请加微信:zhai20050718) 注释: 【1】《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04页。 【2】原文:史疾为韩使楚,楚王问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王曰:“正亦可为国乎?”曰:“可。”王曰:“楚国多盗,正可以圉盗乎?”曰:“可。”曰:“以正圉盗,奈何?”顷间有鹊止于屋上者,曰:“请问楚人谓此鸟何?”王曰:“谓之鹊。”曰:“谓之乌,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国有柱国、令尹、司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洁胜任。今盗贼公行,而弗能禁也,此乌不为乌,鹊不为鹊也。” 【3】《“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十周年:回顾与反思》,网址:http://blog.jiagenliang.mshw.org/post/153/1665 【4】曹峰:《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