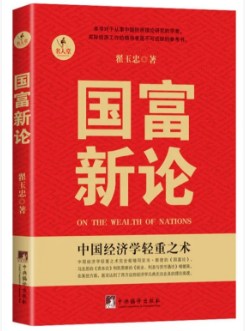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说过,产品的储备是一切社会所共有的。古埃及就有了国家粮库,主管官员的地位相当高。从《旧约·创世纪》中我们能看到,约瑟建议法老在7年丰收之年储备了大量粮食,然后在接下来的7年大荒中将其卖出,从而发了横财。说到底,约瑟的政策只是以王权的名义囤积居奇。 罗马人也有大量的粮食储备,目的和早期中国人一样单纯为了储丰防缺。据历史资料,在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罗马至少有291家公共粮库,储备的粮食足以支撑首都居民7年之需。 西方没有入侵前的印加和印度都有大量的储备。印加人的储备还相当丰富,除了粮食,还有羊毛、棉花和各种金属。 近代,法王路易十四设立了皇家粮食管理局,负责军用粮食的公开采购。美国弗吉尼亚州1632年立法明确要求每一位超过18岁的农民都应当为公共粮仓贡献粮食。 由于西方世界的储备最多停留在储丰防缺的“积谷防饥”阶段,所以西方学者们对储备的见解亦有天壤之别。莱勒认为储备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减少;马克思则持相反的见解,认为储备的三种形式(生产资本的形式,个人消费基金的形式,商品储备或商品资本的形式)就绝对量来说可以同时增加,但是一种形式的储备会在另一种形式的储备增加时相对地减少;西斯蒙第认为储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缺陷;亚当·斯密则认为储备是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现象,农业经济社会历来都是吃上顿不管下顿——显然他不是对评论对象无知,就是在信口开河! 人类文明史上,只有中国人将储备作为政治经济、金融思想的核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本商品的储备,二是与商品直接联系的货币的发行。至晚在春秋时代,基本商品的储备和与商品直接联系的货币发行理论已经相当成熟。 就如同中国人在三千年前就接受了负数概念而西方人到19世纪还称负数十分荒谬一样,笔者认为西方政治经济学长期关注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而没有关注储备的原因是他们的思维方式的与中国人不同。在系统论诞生以前,西方人缺乏从整体角度思考事物的能力,西方政治经济学总是力图从生产或消费方面阐述问题,很少意识到从生产与消费平衡的整体角度阐发问题——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常平仓制度引入西方后,商品储备及与商品直接联系的货币才正式进入西方经济学家的视野。 《逸周书·文传解第二十五》重视储备,但主要还是从积谷防饥的意义是阐述的。上面说,天有四种灾祸:水灾、旱灾、饥年、荒年。灾祸的到来没有固定时间。如果不从事积蓄,用什么来防备它?《夏箴》里说:“平民百姓没有足够吃两年的粮,遇上饥荒,妻子儿女就不属他所有了;大夫没有足够吃两年的粮,遇上饥荒,奴隶侍妾以及车马就不属他所有了;国家没有足够吃两年的粮,遇上饥荒,百姓就不属它所有了。”警惕啊,不思考不实行,灾祸就不远了。(原文:天有四殃,水旱饥荒,其至无时,非务积聚,何以备之?《夏箴》曰: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国无兼年之食,遇天饥,百姓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无日矣。) 《管子·山权数第七十五》的作者认为唯有丰足的储备才能掌握天时的变化。通过大量的商品储备,政府可以防止自然灾害和私商投机影响正常的社会生活。上面引管子言:“商汤在位时有七年旱灾,夏禹在位时有五年水灾。人民没有饭吃以至有出卖儿女的。商汤只好用庄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夏禹只好用历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所以,君主对于天时水旱不能掌握防备,人力和土地财物也都无从掌握了。因此,成王业的君主总是每年贮蓄粮食十分之三,三年多就能有相当于够吃一年的储备。三十七年就能有相当于十一年多一点的储备。每年贮蓄三分之一不至于伤害民生,还可以促使农民重视农业并勤奋努力。即使天灾毁坏土地生产,发生凶旱水涝百姓也不会有死于沟堑或沿街乞讨的了。这就是掌握天时以对待天的权变的办法。’”(原文:管子对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米+亶]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米+亶]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米+亶]卖子者。故天权失,人地之权皆失也。故王者岁守十分之参,三年与少半成岁,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与少半。藏三之一不足以伤民,而农夫敬事力作。故天毁埊,凶旱水泆,民无入于沟壑乞请者也。此守时以待天权之道也。”)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计然的储备原则,以及如何用储备调节市场。计然明确指出,国家绝对不能如投机商一样囤居以求高价(不能学约瑟和埃及法老),要根据市场价格的波动及时平衡物价。计然的经济观念显然远远超越了“积谷防饥”这个层次。司马迁引用计然的话说:“积贮货物,应当务求完好牢靠,没有滞留的货币资金。买卖货物,凡属容易腐败和腐蚀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险囤居以求高价。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情况,就会懂得物价涨跌的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即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即时购进,视同珠宝。货物钱币的流通周转要如同流水那样。”(原文:[计然曰]“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司马迁还说,越王勾践按照计然的策略治国十年,越国就富有了,终于报仇雪耻,灭掉吴国,称霸中原。 (本文摘自翟玉忠《国富新论:中国经济学轻重之术》,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