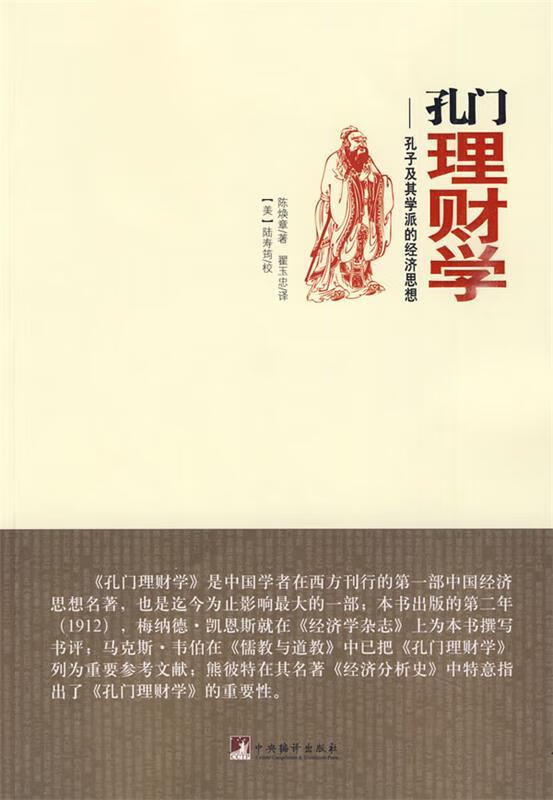长期以来,“利”一词用得很宽泛。在古代,它包括利息、风险保险和管理者的工资。的确,除去了用于生产的开支,所有的收益都可以统称为利。对于农民,它甚至包括地租,因为除了向政府交土地税,他不向任何人交租。甚至包括工资,因为农民自己是劳工。因此,我们必须理解“利”一词的外延之广。既然“利”一词用于企业家的纯收益仅仅始于F.A.Walker,那么该词在古代中国被宽泛地应用就不足为奇了。 (一)罕言利 《论语》告诉我们说,孔子极少言利,【1】这一说法是真实的。司马迁指出了其中原由。他说:“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2】因此,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3】的确,孔子怕人们太注重私利。到了孟子时代,利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因此,孟子不仅很少用“利”一词,还猛烈地谴责它。这些事实说明,儒家的经济原则是从社会和伦理角度出发,而不单单从经济角度出发。 (二)利的正当性 尽管孔子很少谈到利,但他不反对庶人取利。《诗经》上说:“如贾三倍,君子是识。”【4】这说明取利是商人的正当事务,但对于君子、官员则不是。这是对像商人那样取利的官员的谴责,而不是对商人的谴责。对所有庶人来说,无论是农民、手工业者还是商人,获大利都是正当的事,这为孔子所认可。 甚至是自己的学生,孔子也不谴责他们赢利。我们已经知道,子贡是当时的一位大商人,是商家的初创者。一天,孔子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5】回是颜渊的名,赐是子贡的名。大多数注家说孔子赞扬了颜渊,讽刺了子贡,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孔子确实赞扬了颜渊,但他也赞扬了子贡。颜渊以美德知名,子贡以其能力知名。在孔子的这一评述中二人都得到了赞赏。当然,子贡与颜渊相比,颜渊比他好。但当他同孔子的所有其他学生比较时,子贡仅次于颜渊,位居第二。因此,孔子首先赞扬了颜渊,说他近乎有完美的道德。他接着赞美了子贡,说他不安于天命,他的投机常常成功。让我们想想,不接受天命、在投机中常常成功是多么困难啊!这说明了子贡的能力,孔子高度赞赏它。从道德的角度看,颜渊最好,因为他有最好的智能,但不关注自己的经济生活。从智力的角度看,子贡是一位十分有能力的人,而他的德行也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孔子这一评述的真正意义。现在,就算我们承认他丝毫没有称赞子贡,他也没有丝毫反对他。因为,将子贡和颜渊作比较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对,另一个错。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确实认可了子贡的取利。即使他没有这样说,但他也确实没有谴责它。 在《盐铁论》中,子贡得到了辩护。上面说子贡是用自己的资本,不一定从人们那里取利。他只是用自己的大脑,按照市场环境交换商品,在不同的价格间取利。从这一点上说,利是灵活交易的结果,它不定取之于民。 (三)利润额 既然利润额是不确定的,我们无法算出利润率。然而按照古书的说法,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概念。如上面刚刚看到的,《诗经》上提到百分之三百的利。《易经·说卦传》中也提及市场上三倍的利。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古代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被认为是相当好的了。但它还不是特别高的利润。 《战国策》中有一段话谈到利润率:(吕不韦)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6】由此判断,战国时期的利润率十分高。然而这样高的利润率始于春秋时期。管子说,商人能得到相当其资本百倍的利润,为了防止这一点,一个统治者必须有十倍的利润。这里,他的意思是说,统治者作为国家的代表必须取利以调节社会财富,而取得超额利润的私商应被阻止,因为他们伤害穷人,破坏财富的均平。总而言之,周代的利润率十分高,不过当时“利”一词包括了许多因素。 注释: 【1】参阅《论语·子罕篇第九》。 【2】《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意为:唉,谋利的确是一切祸乱的开始呀!孔夫子极少讲利的问题,其原因就是经常防备这个祸乱的根源。 【3】《论语·里仁篇第四》,意为:为追求利益而行动,就会招致更多的怨恨。 【4】《诗经·大雅·瞻卬》,意为:商人唯求三倍利,持政事岂相宜? 【5】《论语·先进篇第十一》,意为:颜回的学问道德接近于完善了吧,可是他常常贫困。端木赐不听命运的安排,去做买卖,猜测行情,往往猜中了。 【6】《战国策·秦策五》。 (节选自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翟玉忠译,陆寿筠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