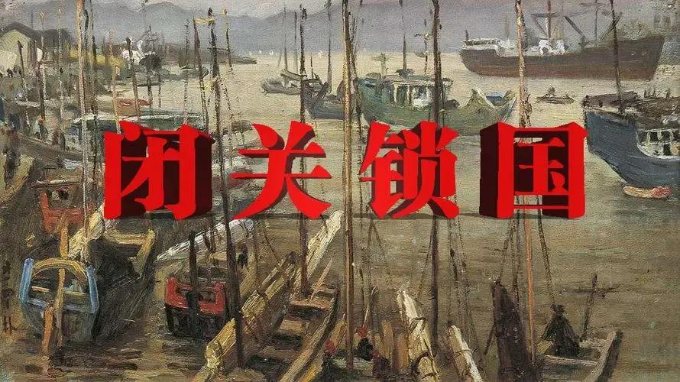三、其他限制政策 1.限制船只大小 可以肯定,以举国之力建造的郑和宝船远大于前代,并且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好的船。不过,永乐时虽有郑和下西洋之举,却限制民间出洋贸易,一项具体措施就是限制民间海船,甚至曾下令“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30)嘉靖“倭乱”时期,明政府禁止制造双桅以上大船,当时闽浙巡抚朱纨规定:“其福州等处原编民间卖谷船只……定以三百石为率,长不过四丈,阔不过一丈二尺,深不过六尺者,许其自便”[12]。限制船只大小,是因为船小则不能航行外洋。隆庆开海自然也取消了船禁。当时按船宽分三等收饷:一丈六尺,一丈六尺到二丈六尺,二丈六尺以上。据张燮《东西洋考》所载,当时由月港出海之船,“大者广可三丈五六尺,长十余丈。小者广二丈,长七八丈”[13]。另据《觚剩续编》载:海瑞之孙海述祖曾“斥其千金家产,治一大舶,其舶首尾长二十八丈以象宿,房分六十四口以象卦,篷张二十四叶以象气,桅高二十五丈曰擎天柱。上为二斗以象日月,治之三年乃成,自谓独出奇制,以此乘长风,破万里浪,无难也”。(31)可见,已不再按原规定限制船只大小。 清初海禁时期,同样限制船只大小。顺治十二年(1655年)规定,不许打造双桅大船。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禁”之初仍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32)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时虽允许打造双桅船,但限定“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舵水人等不得过二十八名”。(33)此外,还曾禁止内地商人在外国打造船只,禁止将船卖给外国。不过此类规定并未严格执行。 2.限制出口货物 在任何时代,统治者都对民人拥有和买卖商品有一定限制,都有“禁物”。按照《唐律》:“禁物者,谓禁兵器及诸禁物,并私家不应有”。(34)“禁物”当然不能进出口,不得“出外境”或“下海”。而且在对外贸易中,除一般的“禁物”外,还常常对国内不禁的货物加以禁止或限制。《大明律·兵律》与《大清律·兵律》一字不差地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下海者,绞”。仔细查检明清两代各种律、例、典、录等文献会发现,“禁物”包括的范围相当广泛。只看相关文字之有无,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几乎囊括所有想象得到的物品。统治者真正希望禁止或限制并另行发布政令,采取一定措施切实限制出口的货物种类也很多。一般来说,兵器(包括硝、磺)、禁书、皇家专用品、毒品(鸦片等)当然在禁物之列,粮食、金属(金、银、铜、铁、铅“五金”等)也属于常规性禁止出口之物,禁止或限制出口的书籍也较一般的“禁书”宽泛,包括史书、地图等。 在有些时期,针对某些特定交易对象,还禁止或限制丝、茶、大黄等商品出口。限制茶叶、大黄出口的原因是时人认为这两种商品是夷人必需之物,不出口(或以不出口相威胁)可达到“制夷”目的,明朝时常以此种手段(限制的商品还有盐、铁器等)对付西北游牧民族,用来对付“西夷”则只是一些人的设想,并未真正实行。“一口通关”时期禁止皖、浙、闽经海路“贩茶赴粤”,(35)目的并非禁止茶叶出口,而是经陆路运至广东再出口。对于丝及丝织品,尽管《大明律》、《大清律》都载有禁止出口的明令,却一直是大宗出口商品。例外的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以“江浙等省丝价日昂”,禁止丝及丝织品出口,只特准前往日本办铜之船搭带限量丝绸。后来发现丝价并未因此而平减,便逐步弛禁。 明清政府对出海船只携带的物品特别是粮食、武器也有限制。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禁南洋贸易”时规定:出洋者“每日各人准带食米一升,并余米一升,以防风阻”。康熙年间曾严禁出海商船携带武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还曾重申:“沿海各省出洋商船,炮械军器概行禁止携带”。后来认识到,出洋船只需要一定的武力自卫,允许带少量武器。雍正六年(1728年)规定:“鸟枪不得过八杆,腰刀不得过十把,弓箭不得过十副,火药不得过二十斤”。雍正八年(1730年)又允许每船带炮不得过二门,火药不得过15千克。嘉庆七年(1802年)允许“出海贸易船只”根据“梁头丈尺”确定“携带炮位”多寡。(36) 相比之下,明清时代对进口货物的限制较少。当然,除一般性“禁物”不许私下进口外,也有一些特例。如明清律令中都视“私下收买贩卖若苏木、胡椒至一(或二)千斤以上者”为犯罪。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禁民间用番香”。在朝贡贸易中对使团携带商品种类和数量也有限制。最重要的是清代对鸦片进口的禁令,却又越禁越多。此外,对一些禁出品是鼓励进口的,如银、铜、硝、磺、粮等。相反,一些外国当局也鼓励中国禁止出口品的输入,如1589年8月9日,菲利普二世训令菲律宾总督,准许对中、葡、日等国商人输入的粮食、军需品、军需品制造原料等物资予以免税待遇[14]。 3.行商制度 中国自古就有“牙行”、“牙商”制度。明初只允许朝贡贸易,当时“贡舶与市舶一事也。凡外夷贡者皆设市舶司领之,许带他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矣”。(37)市舶司既是官府,也是官办商业机构,其管理者是国家官吏。随着民间贸易的发展,市舶司也更多地涉足于民间贸易,承担了海关的职能。到明末,有“三十六行”代纳进口税,市舶司“安坐而得”。清代开放海禁后,对朝贡与民间贸易做了区分。改“以贡代市”为“贡市并举”。通商口岸不设市舶司,改设海关,同时沿袭明末“行商”制度[15]。 “行商”常被人们称作“十三行”或“广东(广州)十三行”[16][17]。实际上,广东的行商不限于十三家,有时多有时少。而且“行商”不限于广东,如清人周凯撰辑的《厦门志》载,道光元年,厦门(福建)有十四家洋行,承担着与广州十三行同样的职能。宁波(浙江)等海关乃至恰克图等陆路贸易中也有此类行商。这些“行商”(亦称洋商、保商)是特许商人,政府授予他们对外贸易垄断权,承销外商进口货物,替外商代购货物,划定进出口货物价格,同时也承担代征税饷,管束外商及办理与外商交涉事宜。外商只能通过他们才能与其他商人、民众和政府官员发生关系,甚至海关官员也不直接同外商打交道,而只能由行商居间转达。不过从根本上说,行商仍然是商而不是官,尽管他们常常通过捐纳拥有虚衔。 4.对外国商队、商船和商人的限制 明清政府都明文规定:凡外国商船来广州进行贸易,必须向(明)市舶司或(清)海关领取进入“部票”(入港许可证),由中国方面指定通事、买办和引水员。清初到广州的外国船只只许停泊澳门,不许进入广州。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始准停泊黄埔。商船入港后,须卸除船上军火炮位。护卫兵船,只许停在虎门要塞以外洋面。 “一口通商”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定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五款,嘉庆十四年(1809年)和道光十五年(1835年)又分别颁布《民夷交易章程》和《防夷八条》。主要内容是:(1)不许夷人在广州过冬。(2)夷人在广州只能住在行商各馆,如行馆房屋不敷,由行商租赁房屋并拨人看守。毋许汉奸出入夷馆。毋令番厮人等出外闲行,如夷商有事必须出行,须由通事、行商随行约束。乾隆末年,始准每月三次到陈家花园(后改花地)和海幢寺二处游玩,但要洋行通事随行。(3)禁止内地民人借领外夷资本。(4)禁止夷人雇请内地之人为其传递信息。(5)派兵于洋船收泊进口处加强稽查,俟其出口后方能撤回。此还严禁夷人进入中国内地,夷人不得带番妇番、哨人等至省,夷商携带番厮不得过五名。不许携带凶械火器赴省,不得偷运枪炮,不得买卖违禁货物,不得乘轿,不得私雇中国人使役,限制商馆雇用民人数目,不许与行商以外的中国商人直接接触。(38) 对中国商民出海贸易也有严格的管理措施。如要求出海商民登记、取具保结、领取船引(票、照)和腰牌,注明船只丈尺、客商姓名、在船之人年貌、籍贯,出海情由、载何货物、往某处贸易、往返日期等。要求已出洋的商船商民按期返回,对未能及时回国者施加惩罚或限制归国。 四、限制性政策的执行 1.政策执行中的微观经济行为 首先,在考虑限制性政策的执行之前,需要澄清政策本身的有无。中国古代律、例、典、录等文献浩如烟海,各代制度、律令多是“萧规曹随”,有些甚至可追溯到上古圣贤,不管是否执行均不加遗漏地抄录。所载“禁令”极多,包括范围极广。只看此类文献上相关文字之有无,可谓无所不禁,无所不限。事实上,很多此类文献不过是“仅供参考”的“文献汇编”,在此中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并无实际意义。而且在中国,很少明令取消祖宗之法、前朝律令者,包括某些作为应急性政令的“权宜之法”,常常也只是悄悄地不再执行(明令取消可能被视为大逆不道)。实际政策却是不断变化的,甚至“初一十五不一样”。只看典籍上相关律令之有无,则不独明清两代从头到尾地“闭关锁国”,而且自秦以来历代皇朝“没一个好东西”。即使在人们认为海外贸易相当自由的宋元,也同样存在海禁律令。其次,有些禁制原本就不是为禁而设,而是为了统治者有选择地提供特许,“使利权在上”。(39)通过特许权的分配,体现统治者的存在感,提高被统治者的向心力,稳固集权者的统治,并更方便地收取更多的“租”。最后,禁制的设置与执行是两回事。禁制虽然无处不在,却无处不可通融,而且弹性十足,有法不依是必然的、普遍的现象,毕竟那是一个“人治社会”。(40) 禁制与违禁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之所以禁,就是存在禁的对象。每次重申禁令,都与此前有被禁之事有关,这一点在诏令中多有体现(参见各相关诏令)。例如,明初与清初均有海上敌对势力存在并进行着大量非法贸易活动,因此也是海禁令集中颁行之时。明嘉靖时期是走私、海盗活动极盛之时,清初“迁海令”是由于此前的海禁令未达预期效果,乾隆“一口通商令”则发自英、荷等“红毛夷”转向浙江口岸之时。另一方面,无法则无违法,禁制越多,违禁者越多。禁制类似水坝,水坝的存在加大了不同河段水位的势差,禁制则制造了超常的违禁之利,禁愈严,违禁之利愈大,违禁的诱惑或动机愈强。至于明清一些主张开海的大臣所描述的海禁造成的悲惨局面,很可能有夸大之辞,禁海之时之地的商民不可能都是饿死也要守法的良民。而且,即使统治者想要完全地“闭关锁国”也做不到,古代政府查禁走私的能力远不如现代,走私贸易的比例远大于现代,与战乱相伴的严厉禁海时期就更是如此。而且,禁制的有效性会依时间变化,一种禁制初行之时可能较有效,随时间推移则会效力递减。 钱通神更能通官,盗有道理也有道路。从商民的角度就有二种方式突破禁制:一是以和平方式从事违禁活动。违禁者可以利用各种漏洞避开禁制,收买贿赂执法者或直接与执法者合作从事官商勾结的违禁活动,执法者本身也常常直接从事违禁活动。二是以暴力方式突破禁制。在海禁严厉时期,常常也是海盗走私盛行之时,如嘉靖年间。这两种违禁的海上贸易活动在整个明清时代都普遍存在,大量诏令、奏折、刑事档案、方志、族史、游记、杂记等均有记载。 清初,东南沿海有数股反清势力从事大规模海上贸易。康熙开海后走私贸易与合法贸易并存。康熙后期“大海商风波”的所谓“大海商”张元隆,就既从事合法贸易也从事违禁活动。甚至“封建皇帝”也认识到:私下的海上贸易无法根绝。例如,康熙二十三年谕曰:“边疆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念,今虽禁海,其私自贸易何尝断绝?今议海上贸易不行者,皆由总督、巡抚自图便利故也”[18]。至于后来规模庞大的鸦片贸易更完全是违禁的。清代尽管没有产生明嘉靖年间的王直和明末郑氏集团那种强大的海上武装商团或海盗,但亦盗亦商的武装走私集团从来就没有绝迹。清初有郑氏、尚可喜等各势力及其沦落为海盗的余部,郑、石、马、徐四姓为首的疍家海盗持续时间更长,乾隆末年和嘉庆年间粤闽地区海盗活动更形成了一个高潮。 如同禁海令一样,其他限制也是可通容的,甚至是形同虚设的。即使是对“红毛夷”,所谓“一口通商”也未严格执行,1757年之后,厦门、宁波仍有少量西洋船只停泊,甚至乾隆本人也曾对此表示宽容。对船只大小的限制实际只在个别时期和地区实行,而且所谓外国商船也不全是外国人的,外资企业中常有中国人参股甚至完全为中资假冒。至于对日本或南洋某个航线的禁令,根本就不具可操作性,官府如何替茫茫大海上的船只把握方向?藏匿、夹带违禁货物、人员更是稀松平常之事。对外国人的限制同样如此,不仅执行者常常懈怠,而且外国人也懂得贿赂,也知道“在中国,很少有花钱做不到的事情”[19]。来到广州的外国商船军火炮位“听其安放船中”。一个英国商人说:“我们实际上是爱上哪里,就上哪里,爱呆多久,就呆多久,而且从来不带通事”。鸦片战争前夕,一个英国人在福建、浙江一住半年并说:“没有一个人敢撵走我们。夷人不许上岸,我们却是进城,四处都跑遍了,中国官老爷绝没有采取措施加以阻止”。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更长驻广州。另一商人说:“禁令只是记录在案,事情仍然照常进行,顽夷仍然和那些以最低价格出售货物的商人进行贸易”。中外商人间的债务同样是越禁越多,不少行商正是因所谓“行欠”而破产[6]。道光十年(1830年),英国下议院对在广州从事贸易的商人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19]。至于鸦片更是众所周知,部分是违禁贸易。 2.政策执行的宏观效果——贸易量的增长 由于认定明清时期是“闭关锁国”的,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明清时期海上贸易有所缩减,不如宋元发达。这显然是误断。有关文献显示,除受战争因素严重干扰时期,明清海上贸易呈持续增长趋势。 明代前期,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宋元时期大体相同,出口以丝、瓷为主,进口则以香料和各种奇珍为主。这种结构,特别是进口品基本上为奢侈品,限制了海上贸易的规模。而主要贸易对象也一如宋元,仍是以周边国家为主,除下西洋的郑和船队外,与欧洲的贸易仍主要通过阿拉伯人进行。明代中期,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欧洲人相继进入亚洲与中国直接贸易。这显然为中国的海上贸易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而此时明廷对民间海上贸易的限制已逐渐松弛。16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日本和美洲相继开始大规模开采白银,大大提高了日本和欧洲人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支付能力,突破了海上贸易发展的另一限制性因素。 明初,洪武、永乐年间尽管对民间海上贸易限制较严,但走私贸易是不可能禁绝的,而且这两个皇帝均热心推动朝贡贸易,永乐年间还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无论郑和出洋目的何在,但公认的是,郑和船队及下西洋完成的贸易规模不小,单只进口的苏木甚至用了数十年,其用途还包括代替官员薪俸,可见进口规模之大。自宣德年间对民间贸易的限制已松弛,嘉靖年间民间贸易形成高潮,隆庆开海后海上贸易更进一步发展。白银的大量流入,证明了海上贸易的增长。到万历年间,进口的白银终于积累了足够的数量,并于万历九年(1581年)全面推行了历史性的一条鞭法改革,确立了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的银本位制度。对于银矿贫乏的中国来说,没有海上贸易的发展,银本位制度的建立是不可想象的。明末时期,尽管明政权失去了对海上贸易的控制,但海上贸易仍持续发展,郑氏集团的规模为此提供了充分证明。东南亚欧洲殖民当局的一些文献从另一方面提供了明后期海上贸易发展的证据。“据统计,万历十六年(1588年)以前,从广州出口到马尼拉的货物总值为22万西元,其中丝货量值为19万西元;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丝货值达到25万西元。崇祯九年(1636年)以前,每艘开往墨西哥的“大帆船”,登记运载中国丝货为300—400箱至500箱”。“万历八年至十八年(1580-1590年),每年运往果阿的丝货为3 000担,价值银为24万两,利润达36万两;崇祯九年(1636年)丝货达6 000担,赢利72万两”。当时,不仅日本、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穿上了中国丝绸,而且东南亚土著、墨西哥印第安人和黑人也都普遍穿着中国的丝绸与棉布服装[20]。 与明代相比,清代海上贸易在结构上又有新变化。从出口商品结构上说,最重要的变化无过于茶叶成为大宗出口商品,并成为第一大宗商品,与此同时,茶叶的出口带动了瓷器出口的进一步增长,丝绸出口的绝对量也有所增长。进口商品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是鸦片通过走私流入中国,以至阻滞了白银的流入。在贸易对象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对西方贸易比重进一步扩大,继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之后,欧美国家相继加入与中国的直接贸易,更具实力的英国成为最重要的贸易对象国。 清初,如果不将郑氏算作外国人,中国的海上贸易仍保持了相当大的规模。而自康熙开海后,海上贸易量是持续增长的。康熙开海后的清代,对海上贸易的监管较明代有效得多,相对于未进入官方视野的“走私贸易”,“合法贸易”的比例有所提高,因而也有了更靠谱的统计数据。很多文献[21][22][23]都列有虽不完整,但足以说明海上贸易持续增长的相关数据。也有不少学者专文论及这一时期海上贸易数量持续增长的趋势。如黄启臣曾从贸易港口的扩大和贸易国家的增多、商船的数量不断增加、进出口商品数量繁多和贸易商品流通量值的增加四个方面论述了康熙开海至鸦片战争前夕清代海外贸易的发展[6]。由于相关文献已有相当充分的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只需指出:无论进出口商船和吨位数量,主要商品数量和种类,主要贸易对象国的贸易量,白银流入量,进出口总值以及海关税收,都体现了海上贸易的增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魏源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中以当时中国少有的方式,给出道光十七年(1837年)粤海关各种主要进出口商品的数量,并计算了该年粤海关的海上贸易规模:由粤海关进口的商品总值为2014.8万元。除此之外,英国人输入的鸦片价值达2 200万元,加上美国等国商人输入的鸦片就更多。年出口商品总值为3595万元。 (作者系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来源:《财经问题研究》2012年第11期) 注释: (30)《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七,永乐二年正月辛酉。 (31)钮琇《觚剩续编》卷三,事觚:海天行。 (32)《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刑部五四,兵律,关津,北京,中华书局,1991。 (33)《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二○,吏部一○四,处分例。 (34)《唐律》卫禁、擅兴律、关市令对禁物有相当详细的规定。 (35)《粤海关志》卷十八,禁令二“茶之禁”。 (36)见[清]周凯撰辑《厦门志》(卷五.船政略.商船;洋船(附洋行))。此处除载有前述中央政府的规定外,还说明了一些相关的地方政策:“省例:乾隆二十二年,闽省渔船自十二年议准带食米一升出洋者,余米一升。嗣因浙省米贵,每人每日余米之外,再预带六升;价平,仍循旧例。是商船准带米一升五合、漁船准带米一升;台湾商船准带食米六十石,是以二十人十日计算也”。 (37)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二六,市籴考二。 (38)参见《粤海关志》卷二八,夷商三;卷二九,夷商四。 (39)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一,北京:现代出版社,1991年。 (40)“法治社会”至今仍未建成,如何苛求“封建统治者”?
参考文献: [12]朱纨.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7.2166. [13][明]张燮.东西洋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4]菲律乔治,薛澄清.西班牙与漳州之初期通商[J].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4). [15]李云泉.明清朝贡制度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16]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初版于1937年)[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17]梁方仲.梁方仲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1200. [19][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M].康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66. [20]樊树志.晚明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21]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Z].北京:中华书局,1962. [22]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Z].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23][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