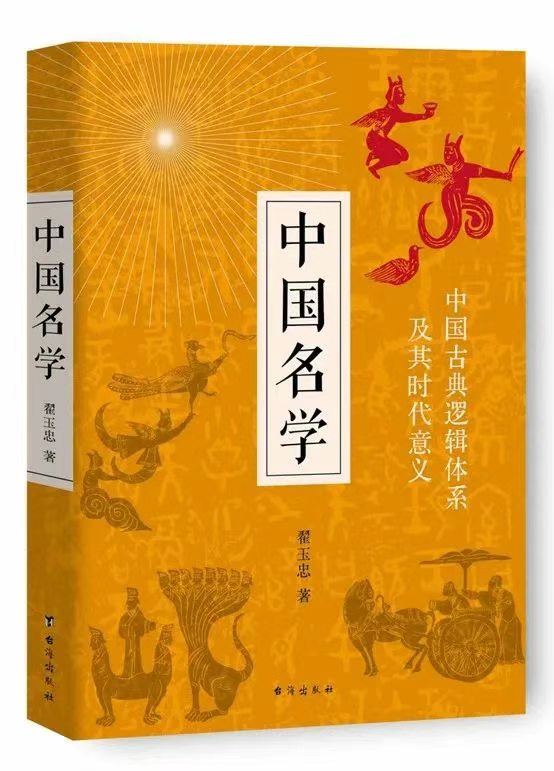所谓“一宗”,就是名学的基本宗旨——正名。 名学的基本宗旨在正名,《墨子·小取篇》“以名举实”是也。《墨子·经说上》也说:“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 正名的具体方法《公孙龙子·名实论第一》概括无遗。上面说:“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伍非百先生释曰:“谓正之目的,在正其实。如何正实?在正其名。如何正名?在唯乎其谓。如何唯乎其谓?在唯乎其彼此。”【1】那么什么是“唯乎其彼此”呢?就是《公孙龙子·名实论第一》所说:“彼彼当乎彼,则唯乎彼,其谓行彼。 此此当乎此,则唯乎此,其谓行此。”“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 现存《公孙龙子》诸篇,都是围绕正名原则提出的论题,看似违反常识,实则在训练思维的精确性。如《白马篇》中的“白马非马”,就是要我们知道白马并不等同于马。庞朴先生解释说:“古人对马的毛色特别注重,如白马多用于盟誓和祭祀,他色马则不能。公孙龙借此指出颜色对于马的重要性:颜色既能使黄、黑马不等于白马,那么白马的白色,也应使它不等于马。”【2】 现代西方生物学将电子显微镜下的生物切片等同于生物体本身,现代西方医学将用于解剖的死人等同于人(中医不是这样,中医讲 “因变以正名”),尽管过去数百年来西方科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上述还原论思想也产生了严重的问题,使人看到了还原论的局限性。【3】 学人已经习惯于将正名之“名”等同于西方逻辑学中的“概念”,这是错误的。名是基于具体事实,而“概念”则是基于抽象的思维形式。在名学中,所有联系实的言说都是名,故《荀子·正名篇》说:“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名是用来联系事实的;在社会治理中,名指名位,名分,社会责任,甚至“陈言”也是名。《韩非子·二柄第七》论循名责实说:“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这里“陈言”就是名,“事功”就是实,名副其实,则赏,名不副实,则罚。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理论的精髓全在于此!难怪《吕氏春秋·审分》说:“正名审分,是治之辔已。故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放悖。夫名多不当其实,而事多不当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审名分也。” 所谓“二辞”,就是名学的基本推理形式,“立说轨范”:谓、故。 《墨子·经上》有“使,谓、故”一条,“(说)使 ,令谓。谓也,不必成、湿。故也,必待所为之成也。 立说包括两个方面:谓辞和故辞,谓辞是表达所然的,故辞是表达所以然的,分别相对应于《墨经》中的“经”和“说”。庞朴先生解释说:“使,就是令(令谓),就是举出,提出(供争辩的命题)来。大别之有两类:谓和故……这里说的‘不必成、湿’,意思是,谓只是表达一种看法,一种意思,它未必能成立,也未必不成立(‘湿’,关西方言,不成)。‘故’却不然,它是立论的根据,必待的条件,不可缺少的后盾。这也就是说,谓是所然,故是所以然。”【4】 伍非百先生多方阐发名学这一“立说轨范”。他解释“使,谓、故”一条说:“此言使有谓、故二义。使,假设也,犹今言‘立意’,《大取》谓之‘立辞’。《经下》云:‘使,假义,说在使。’说曰:‘使,令也。’令,亦假设。故曰‘使 ,令谓’,令谓,犹云使之为言令也。《墨经》无‘辞’字,以‘使’‘令’等字代之。‘谓’,所然也,立说所表示之意义,当今因明之‘宗’……‘故’,所以然也,立说所依据之论证,当今因明之因喻等……此条言‘说’所立之‘辞’有谓、故二种。”【5】 “言‘辞’有谓、故二种。一为所立者,二为所以立者。以因明例之。谓,当因明之宗。故,当因明之因。‘宗’,为随所欲立,其能成立与否,可不必计。‘因’,则非能立者不可,故云‘必待所为之成’。‘以说出故’者,谓说之能立,在举出所以说之‘故’。《经》曰:‘说,所以明也’‘以明’即‘出故’。”【6】 需要指出的是,伍非百先生意识到中国名学的“谓、故”结论比佛学因明相关论式、西方形式逻辑三段论更为灵活、简约。他在解释《墨经》“说,所以明也”一条时说:“凡说必具二辞:一曰‘谓’,说者所示之主张也。二曰‘故’,说者所持之理由也。有‘谓’止于可知,有‘故’而后可信。说也者,以‘故’明‘谓’。故曰:‘说,所以明也’。 “按:中国古代名辩家,立说体例,仅存于今而可以为法式者,如《经下》‘……说在……’之文体是也。‘说在’以上,为所示之‘谓’;‘说在’以下,为所持之‘故’。此式大概创始于《墨辩》,而他宗亦间有用之者。如《韩非》之《内外储说》是也。此式之长,在能以简语立宗,而别为说于其后。约说之,则一语已足;详说之,则千万言而不滥。”【7】 名学的“谓、故”直接影响了中国学术范式,它不是以定义和假设为逻辑起点,而是以问题为中心,多方说明之。 (选自《中国名学:中国古典逻辑体系及其时代意义》,该书可在京东、当当上买到;支持我们,欲购作者签名版请加微信:zhai20050718) 注释: 【1】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25页。 【2】庞朴:《中国的名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年,第71—72页。 【3】参阅斯蒂芬•罗思曼:《还原论的局限:来自活细胞的训诫》,李创同、王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4】庞朴:《中国的名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年,第114—115页。 【5】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7—79页。 【6】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