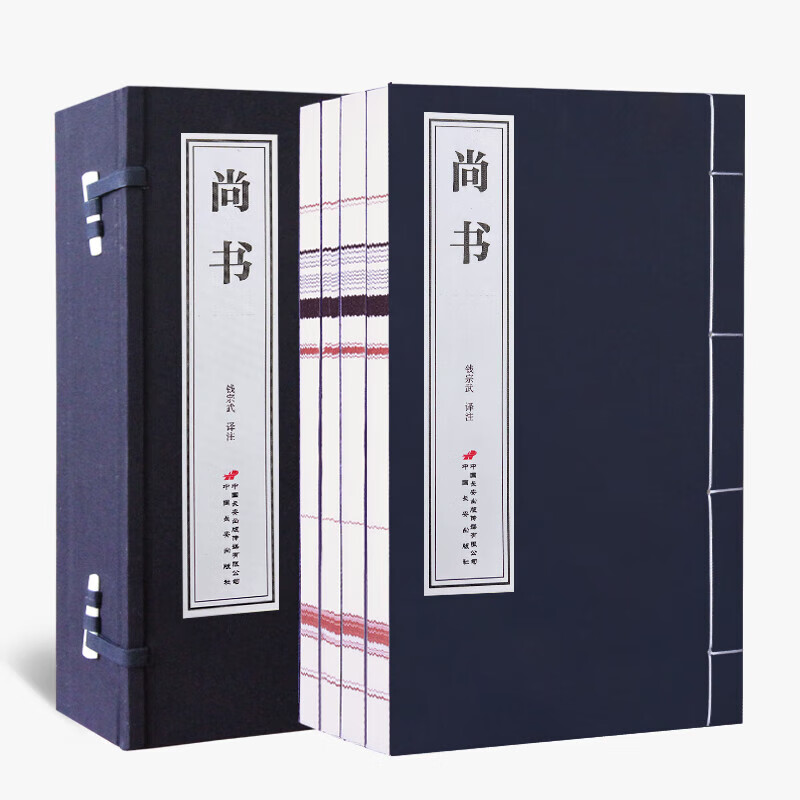“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打开《尚书》,可以在此谛听“舜庭赓歌(赓歌, gēng gē,酬唱和诗——编者注)”,窥探“雅诰奥义”,其中的珍藏,据说“历代宝之,以为大训”,迎面可见的乃中国人对大道的信仰,对历史的虔诚,延续着绵绵不绝的文明根性。在古人看来,历史自有不朽的生命,经之为经,在于“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用今天的话说,包含了文明之真谛、社会之规律。尽管“与时俱进”,具体治理形态“虽设教不论”,内在价值超越时空,“其归一揆”。《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类无论走的再远,也走不出天赋的性灵。诚然,孟子早就告诫:“尽信书不如无书”,提示对历史保持中正的态度,但前提是对自身文化根柢的“温情与敬意”。否则,悍然“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如果把中华文化比作参天大树,我想史是根柢,经是主干,子是分枝,集是繁花:文明总是扎根于历史土壤,所谓“六经皆史”,经典的不朽来自历史筛选而非一时玄想。诸子百家在不同维度伸展,让大树枝干参天,一代代人开枝散叶,而后生机盎然。六经之中,《庄子》所谓“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构成相互补充的整体。先民整理文明精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从人世出发到人世中来,发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中《尚书》被称为“政书之祖”,因为“夫书者,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言之策”,来自历代史官对重大国事活动的记载,保存着历史记忆,提炼着历史经验。难怪中国自古有发达的史学传统,甚至被称为“历史民族”,而又突出“存史资政”的色彩。 汉孔安国《尚书序》云,自上古伏羲“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而文籍生焉”,开始了有文字的记载。历经三皇时代的“三坟”,五帝时代的“五典”,产生了探索八卦奥义的“八索”,汇聚九州风物的“九丘”,历经漫长积累,文化成果蔚为大观,为《尚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其中的主题,恒在传承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之道:“坟,大也,”又说“典者,常也”。比起今人的困顿,先民的富足在于虔诚的信仰。三皇“其道至大”,而“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难怪钱穆先生感慨,比较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的偏好在于“常”。 春秋之世,大乱方起,孔子“有至德而无至位,修圣道以显圣人”,整理历代文化遗产而集大成,力图将天下挽回常轨。从总结尧舜之道开始,“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删繁就简,达到“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的意图,整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从而有了这部《尚书》。历经战国大乱,到了“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的时代,为重开太平奠定了文化基础。汉景时代,济南人伏胜以九十高龄传授《尚书》,奠定今文经学。此后,汉武帝“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意在凝聚共同价值,避免“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上无以持一统”,陷入思想分裂。汉代的成功,《资治通鉴·唐纪》指出在于文化支撑:“汉世尚儒术,宰相多用经术士,故风俗淳厚。”太宗开拓大唐盛世,其理念是“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中华元典始终居于文化传统的中心,塑造着中国人的灵魂,维系着学术人心。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在强大科技力量支撑下涤荡全球,几乎将中国人的信仰连根拔起,掀起了“打到孔家店”的狂澜。文明的现代转型,势必与学术思想的变迁相表里,其间顾颉刚先生提出打破五帝信仰,否则“就使得科学的民族史无法研究”,意在挣脱旧学束缚,重构现代史学,产生了极大影响。但到了疑古末流,几乎无经不伪,祖先也沦为幻影,不啻自戕文化根柢。梁启超先生告诫:“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民族性关乎民族生命,“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故“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历史不幸言中。如今度尽百年洪波,文运复兴势必与民族复兴相伴,“两创方针”与“两个结合”的提出,意味着迎来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回归。我们亟需重读经典,激活其新时代的生命。 所谓“大道之行”,历经无数日出日落,中国人依然坚信“道者,万世无弊”,从来是人类社会“所由适于治之路也”。先民追随先圣一路开天辟地,留下所谓“道统”,延续民族文化的命脉,镌刻在中华元典中。《汉书·艺文志》云:儒家之为儒家,在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从历山到尼山,文脉连绵千载,我们走进历山恰是为了走出历山,延续文脉,回到当下。《尚书》的追述从《虞书》开始,垂下一条祖训,叫做“天下为公”。 《尚书》对华夏文明的记载,从古帝唐尧开始,然而把记录唐尧的“尧典”,纳入了虞舜时代的“虞书”。其中缘故,唐孔颖达《尚书正义》解释为:“尧典虽曰唐事,本以虞史所录,末言舜登庸由尧,故追尧作典”——因为是虞舜史官追记前朝,故纳入虞书。 遍览《尚书》,惟有对尧舜的记载称为“典”。中文所谓“经典”,从词义上看,“然经之与典,俱训为常”,本来都是“皆可为后代常法”的意思。区别在于“经”是中华元典的总称,“典”意味着“特指尧舜之德,于常行之内道最为优”,也就是经典中的经典,难怪中国人几千年来一说最高理想,就是“尧舜之道”。所谓“帝”,本来是对天道自然的一种称谓,取其“言天荡然无心,忘于无我,言公平通远”的精神,由此实现《礼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世界。可见五帝的历史,始终寄托着中华民族天下大同的终极追求。 (胡春雨,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天桥作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