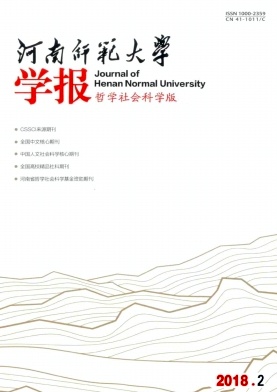三、“任势”是指运用法术、赏罚、毁誉,而不具独立性意义 “势”是“法术势并用说”的症结所在,故对冯氏之说的进一步驳正,要求我们全面审视韩非《难势》原文。 “难势”,专家解释说:“就是围绕着慎到的势治学说进行的辩难。”在《难势》中,参与辩难的一共有三方:首先是“慎子曰”。慎到发难说:“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螾螘同矣。”同理,“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因而他认为:“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接着是“应慎子曰”,是儒家学者对慎到的责难。他们认为,“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威势之利济乱世之不肖人,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因而主张“必待贤乃治”。最后是“复应之曰”,是韩非对儒生们的责难,其文如下: “复应之曰:其人以势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贤乃治’,则不然矣。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今曰‘尧、舜得势而治,桀、纣得势而乱’,吾非以尧、桀为不然也。虽然,非一人之所得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若吾所言,谓人之所得设也而已矣(原文作“若吾所言,谓人之所得设也,若吾所言,谓人之所得势也而已矣”,据俞樾意见改)。贤何事焉……夫贤之为道(原文作“夫贤之为势”,据陶鸿庆意见改)不可禁,而势之为道也无不禁,以不可禁之贤与无不禁之势(原文作“以不可禁之势”,据顾广圻意见改),此矛楯之说也。夫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是犹乘骥駬而分驰也,相去亦远矣。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辩之,不能治三家。夫势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贤’则亦不然矣……且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必苦莱亭历也。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未之议也,奚可以难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议未及此论也。” “势”在韩非书中有两层意思:一是权力。如“无势之谓轻,离位之谓躁”,“势不足以化,则除之”,“势重者,人主之爪牙也”,“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二是形势、趋势,如“为巧文之言,流行之辞,示之以利势,惧之以患害,施属虚辞以坏其主”,“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岁数而又不得见”,“国小无礼,不用谏臣,则绝世之势也”。韩非的“势”是特定概念,是“贤”“势”对立之“势”,故第二层含义的形势、趋势之“势”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列。 冯友兰说:“韩非中的《难势》篇,阐述慎到关于重势的理论,又设为儒家对于慎到的理论的批评,又设为慎到一派反批评。”似乎是说韩非和慎到的“重势”是一回事,这很值得商榷。《难势》篇的主旨不是为慎到理论做辩护,而是借题发挥,提出对“势”的新解。韩非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儒家学者对慎到的批评,承认“尧、舜得势而治,桀、纣得势而乱”。但是韩非认为,问题不在于任“势”,而在于任什么样的“势”。他认为,“势”名称虽一,但可以表达诸多含义,他把慎到的“势”称为“自然之势”。我们知道,通常意义上的君主,只要不是傀儡,都会拥有权力。这种既有的、未经雕琢的权力就是“自然之势”。刘泽华先生指出:“自然之势指在客观的既成条件下掌权和对权力的运用。”其说甚确。韩非认为,“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基于“自然之势”主张“任势”无异于主张太阳会发光,没有任何意义。(注:慎子不会愚蠢到主张太阳会发光,《难势》是韩非设计的对话,意在通过双方“贤”“势”辩难来引出自己的观点。慎子绝非只主张“自然之势”,说见下文。韩非专挑慎子的“势”思想,不过是断章取义,借慎子以张己说。) 韩非主张“人之所得设”之势。所谓“人之所得设”之势,其实是指经过人为精心设计的权力,亦可理解为“在可能条件下能动地运用权力”,学界称之为“人为之势”。韩非未在《难势》篇对“人为之势”做出解释,而在《奸劫弑臣》篇提到了两种“人为之势”。 一是“聪明之势”。韩非说:“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暗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 “聪明之势”的要点是“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这在《难三》中叫做“因人以知人”,韩非在《难三》中批评子产说:“恃尽聪明劳智虑,而以知奸,不亦无术乎!且夫物众而智寡,寡不胜众,智不足以遍知物,故因物以治物。下众而上寡,寡不胜众者,言君不足以遍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韩非批评子产为“无术”,是因为子产“恃尽聪明劳智虑”。韩非所说“术”,是指“因人以知人”,其实就是“聪明之势”。换言之,“聪明之势”是指“因人以知人”的察奸之“术”。 二是“威严之势”。韩非说:“世之学术者说人主,不曰‘乘威严之势以困奸邪之臣’,而皆曰‘仁义惠爱而已矣’……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韩非所说“威严之势”是指“严刑重罚”,与“仁义惠爱”相对立。韩非还说:“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于是犯之者其诛重而必,告之者其赏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众,民疾怨而众过日闻。孝公不听,遂行商君之法,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私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严刑重罚”是指商鞅式的“严刑峻法”。“乘威严之势”是指用严刑峻法治理臣民。 用“聪明之势”就是用“因人以知人”的察奸“术”,用“威严之势”就是用严刑峻法。可以说,两种“人为之势”是指运用“法”和“术”。 现在,我们再来考察《难势》中“人为之势”的含义。一是“法”。韩非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侯外庐等人认为:“韩非赞同慎子的势论,所以特作《难势》专篇为他辩护,借以明‘抱法处势’,不恃尧、舜而治,以此论证法治优于人治,而法与势相得益彰。”“抱法处势”是指“法”“势”并用互补吗?“抱”是表示动作的动词,“抱法”是指使用法令;“处”是表示状态的动词,“处势”是指据有权力。“抱法”为动作,“处势”为状态,没有并用的意思。《八经》有“执柄以处势”,“抱法处势”应是“抱法以处势”的省略,是指使用法令以据有权力。二是“赏罚”。韩非说:“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辩之,不能治三家。”“庆赏”“刑罚”构成了“势”,即“执柄以处势”。“释势”意味着丢掉赏罚。三是“术”。韩非说:“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度量之数”与“隐栝之法”对应,“数”即“术”。韩非批评儒生:“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未之议也。”此处亦有主张“术”之意。综上,君主采用“人为之势”意味着采用“法”“术”“赏罚”,只是表述不太清晰,需要明辨而彰显之。 在《有度》篇中,韩非较为清晰地指出了“任势”的含义。韩非说:“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先王以三者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独制四海之内,聪智不得用其诈,险躁不得关其佞,奸邪无所依。远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辞;势在郎中,不敢蔽善饰非;朝廷群下,直凑单微,不敢相踰越。故治不足而日有馀,上之任势使然也。”不难发现,引文结尾“上之任势使然也”对应的正是前文“先王以三者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任势”是指采用“法”“术”(数)、“赏罚”,其说明矣! 此外,“任势”有时也包括“毁誉”。《外储说右上》的“经一”说:“势不足以化则除之。”“说一”是对“经一”的解释,其解释为:“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势不足以化则除之”是说,奖赏他、称赞他,不足以使他劝勉,惩罚他、谴责他,不足以使他畏惧,那就除掉他。很明显,“势”是指赏、誉、罚、毁。韩非还主张将“赏罚”“毁誉”统一起来:“赏誉同轨,非诛俱行。”韩非还主张:“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因此,毁誉是对赏罚的补充,四者一起构成了韩非“任势”的重要内容。 总的来看,韩非的“任势”,包括了法、术、赏、罚、毁、誉。其实,这六者之间有着严密的逻辑关系:法与术一起构成了“人主之大物”,赏罚以法术为客观依据,而毁誉则依赏罚而行。是故法术、赏罚、毁誉构成了一套精致的权力运作制度。它们实质上是制度化的权力,即韩非的“人之所得设”之势。这套制度使君权运用得以规范化、理性化,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自然之势”的盲目性与随意性。 总之,韩非主张的“任势”,是指运用法术、赏罚和毁誉。“势”是不可能离开法术、赏罚、毁誉而独立发挥其治国之用的,离开法术、赏罚、毁誉,就无所谓处势、任势,即使有势也不能用,亦失之矣。韩非虽然肯定了“势”的重要性,但却否定了“势”的独立性,故“法术势并用说”可以休矣! 四、误判韩非思想体系“法术势核心说”的原因分析 在传统的韩非思想研究中,还由“法术势并用说”发展出一个“法术势核心说”,此说之难以成立前已言及,而何以会造成这一误判,则需要寻其根源。 回到《韩非子》文本,不难发现,无论韩非写文章说什么,几乎都要落实到“法术”。韩非的“法术”主张得不到采用,故他不得不写文章进行多方论证,进而将其主张理论化、体系化,上升为系统化的思想。既然各种论证均围绕“法术”而展开,其思想自然是以“法术”为核心。如果说“法术”是韩非思想的“核心概念”,那么围绕“法术”而展开的概念便是“次级概念”。“贤势之辨”在韩非著作中不过是诸多论证之一,正如上文所指出,“势”最终亦落实为“法术”,故“势”是以“法术”为核心的“次级概念”。除了“势”,这些“次级概念”还有“人情”、“人性”、“道”、“德”、“理”、“赏”、“罚”、“公”、“私”、“名”“利”,等等。 可以说,韩非著作是以“法术”为核心的论证体系,其思想是以“法术”为核心的概念体系。用“法术”二字概括韩非思想,既符合韩非的自我认知,也符合韩非著作的实际情况,而“法术势”反映的只是韩非思想之一隅,既不是韩非思想的核心,也不是韩非思想的概要。 为什么“法术势并用说”和“法术势核心说”均不能成立?从表面上看,其原因是对文献的误读和剪裁,然从深层角度讲,对文献误读和剪裁的原因可能与“先入为主”的认识常规密切相关。事实上,“法术势”理论在创立之初便基于很多预设,在研究方法、研究材料、研究内容上均有重要前提问题值得辨析。 首先,得出“法术势”理论的方法值得商榷。 冯友兰的哲学史研究方法受到了杜威的深刻影响。他说自己的哲学思想“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新实在论占优势”。1923年,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天人损益论》博士论文答辩时,杜威曾向他提问:“这些派别是否有个发展的问题,例如这一派发展到那一派,而不是像一把扇子那样,平摆着?”据冯友兰说,当时他没有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是因为他还没有打算做哲学史研究。反过来讲,等冯友兰打算写哲学史时,杜威就不能不对他产生影响。 冯友兰在评价他的写作背景《中国哲学史大纲》说:“胡适在当时宣传杜威的实用主义,但是限于实用主义的真理论。至于发生法,他很少提起,不过总是受一点影响。”冯友兰所说杜威“发生法”,其实是“进化发生学法”,是以进化论的眼光研究事物的发展。冯友兰将之应用到哲学史研究,是用发展的观点研究哲学流派的来龙去脉。冯著把诸子分为各家各派,于“法家”首先树立“重势”“重术”“重法”的“法家三派”,然后又认为韩非“集此三派之大成”,进而得出韩非思想为“势、术、法,并用”。因而,冯友兰研究法家的思路,体现的正是“进化发生学法”。 然而“进化发生学法”未必适合法家研究,因为该方法预设了一个法家学派,而先秦“法家”是汉人重构先秦学术体系的产物。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虽然划分了“儒”、“墨”、“法”、“名”、“道”,但是司马迁却把韩非、申不害与老子、庄子合传,说他们“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这似乎是说,韩非、申不害是“道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则把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都划入“法家”。两家划分之所以有如此差异,是因为战国不存在一个真正有师承或学派意识的法家“学派”,司马迁、班固只好根据思想共性进行划分。 “进化发生学法”的根本问题在于对法家思想的“发生方式”存在误判。决定法家之所以为“法家”的,是他们在政治主张上的共性,而政治主张又来自对现实政治问题的思考。这也是韩非师承荀子,却不是儒家的原因。既然法家思想主要“发生”自现实政治,那么从学派流变角度探讨韩非思想的“发生”,是不是有点方向不对呢? 其次,支撑冯友兰“法术势”说的材料极为有限。 “疑古”是冯友兰构建“法术势”理论的重要背景。1919年,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指出:“《韩非子》十分之中,仅有一二分可靠,其余都是加入的。那可靠的诸篇如下:《显学》《五蠹》《定法》《难势》《诡使》《六反》《问辩》。” 1927年,容肇祖发表《韩非的著作考》,据他考证,“确为韩非所作者”为《五蠹》《显学》,“从学说上推证为韩非所作者”为《难势》《问辩》《诡使》《六反》《心度》《难一》,其他均不可信。对于“疑古”,冯友兰于《中国哲学史》序中商榷说:“前人对于古代事物之传统的说法,近人皆知其多为‘查无实据’者。然其同时亦多为‘事出有因’。”他后来写文章称其观点为“释古”。然而,在韩非思想研究中,“释古”并没有“走出疑古”。 《中国哲学史》引《韩非子》篇目分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系之于“韩非”的篇目有《八经》《扬权》《外储说左上》《六反》《显学》《五蠹》;第二,系之于“法家”的篇目有《难势》《用人》《有度》《难二》《难三》《问辩》《二柄》《定法》《孤愤》《问田》《解老》《喻老》;第三,既不言“韩非”又不言“法家”,仅仅称引《韩非子》的篇目有《大体》《功名》《人主》。按照“释古”,后两种情况所引篇目均不属韩非作品。《韩非子》可靠篇目,胡适肯定了七篇,容肇祖肯定了八篇,冯友兰竟然只肯定了六篇。廖名春说:“冯友兰的‘释古’貌似中庸,但实质是倾向疑古的。”这个判断基本属实,冯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冯著为什么只认定了六篇为可靠篇目?笔者认为,除了冯氏深受“疑古”影响外,还与“进化发生学法”密切相关。冯著用这六个篇目论证了两个命题:一个是韩非综合“法家三派”而成“法术势”,以《八经》的一条材料证明之;另一个是韩非继承荀子“性恶论”,以《显学》《五蠹》《六反》《扬权》《外储说左上》证明之。可以说,这六篇之所以被鉴定为韩非作品(以及《八经》材料之所以被剪裁),是因为能够找到它们与“法家三派”或荀子“性恶论”的继承关系,而这种继承关系之成立有赖于“进化发生学”对韩非思想来源的预设。然而,“进化发生学”与“疑古”均存在问题:“进化发生学”的问题上文已经指出;至于“疑古”,如今研究者基本达成共识,《韩非子》绝大多数篇目是可靠的,胡适、容肇祖把《韩非子》可信篇目降到最低,是一种极端的做法。 在极有限的材料约束下,冯友兰仅仅论证了两个命题——“法术势”自然是核心命题了。今天我们对材料的认识与过去截然不同,“法术势”在韩非思想中的地位是不是应该重新审视? 再次,“法术势”的理论前提“法术势三派”说不成立。 冯友兰从梁启超那里接来并改造了“法家三派”说,构建了集“重法派”“重术派”“重势派”于大成的“法术势”理论体系。然而,法家是否存在“重势派”,这很值得怀疑。依笔者愚见,所谓“重势派”基本不能成立。我们见到的慎到资料甚少,所谓的“重势派”判断不过来自《难势》“贤势之辩”而已。这个判断本身就有问题——如果主张“任势”就能算作“重势派”的话,那么主张“任贤”是不是意味着还有个“重贤派”?倘若如此,这样的学术划分未免太过随意。 更为要害的是,在先秦学术批评中,《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均不言及慎到“重势”。《天下》提到了慎到“笑天下之尚贤”,却与“任势”无关,而是“齐万物以为首”,对万物作平等关照,顺应万物,“以为道理”,人们应该“舍是与非”“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像“无知之物”(土块)一样,“动静不离于理”,因而无需圣贤。只不过,《天下》作者不承认慎到的“道理”,他借“豪杰”之语评价说:“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荀子评价慎到:“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荀子同样没有提到慎到的“势”。 《天下》与《非十二子》均从整体角度对慎到思想进行总结和批评,两者都没有提到“势”,而《难势》不过引用了慎到的一段话而已,并没有对慎到思想做整体性评价。从《天下》和《非十二子》来看,慎到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因任“道理”而“尚法”。梁启超、冯友兰仅以《难势》的只言片语为依据,便断定慎到为“势治主义”派、“重势”派,是否如陈寅恪所言:“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进化发生学法”、过度“疑古”、“法家三派说”,是冯友兰创立“法术势”理论的前提,而这些前提中除了过度“疑古”近些年有所改变外,它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支配着学术界,这大概是“法术势”理论长期得不到纠正的原因。 结 语 韩非言必称“法术”,而韩非研究者言必称“法术势”。韩非把自己归为“法术之士”“有术之士”“能法之士”,而不说“能势之士”“有势之士”,在与堂谿公的对话中,他亦把自己思想归为“法术”,而不言及“势”。而学界则越过韩非的自我认知,再增添一个“势”,其实是不切实际的自我高估:我们比韩非更懂韩非。然而,学界更需要了解的是自己。 思想史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制约着对诸子的认识,而主体意识除了个人因素外,亦具有一定的历史客观性。两千多年来,人们对诸子的认识大概经历了两次重要重构:一是先秦学术体系的汉代生成。汉代学者不仅整理了先秦典籍,还对先秦学术体系进行了分类,他们对诸子的理解构成了后来学者认识诸子的重要前提;二是先秦学术体系的近代建构。近代学者援引西方研究方法研究儒家、法家、墨家、道家、名家等,他们得出的一些结论又构成了我们认识诸子的重要前提。 所以,我们不但要回到经典,对比学界理论与诸子表述间的异同,找出相关理论对文献的误读、误判;而且需要我们对误读、误判所产生的理论前提进行探究。前代学者的思想成果在后代学者的主体意识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做一番学术史清理很有必要。在“法家”研究领域,汉代学者、近代学者的研究构成了我们认识的前提。对他们的研究进行反思,对于当下“法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贾坤鹏,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先秦史学会法家研究会副秘书长 本文原载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77-84页,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