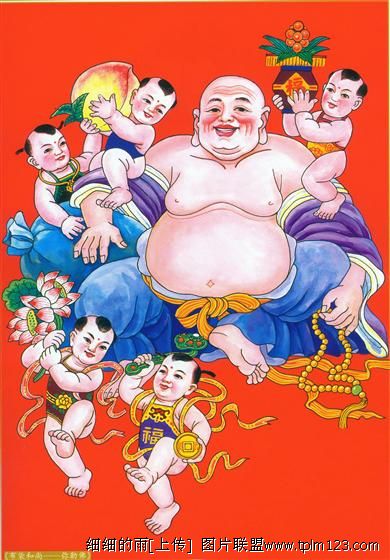摘要:偏执,是明代政治领域道德生活的基本倾向。由于对祖宗家法的偏执遵守,对儒家道德理想的偏执追求以及对宦官的偏执认识,当然也包括张居正自身所具有的偏执精神,最终导致了张居正悲剧的发生。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自幼聪明好学,16岁便高中举人,23岁中进士,旋即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穆宗隆庆元年,在首辅徐阶的推荐下,晋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开始进入内阁。神宗万历元年,张居正成为首辅。由于得到了神宗皇帝和慈圣太后的高度信任,张居正在内阁首辅的职位上便开始实行以整顿吏治为核心,包括财政、武备、边防等方面的改革运动,短短几年,就实现了“海内肃清,四夷服”、“纪纲法度,莫不修明”(《明史·张居正传》)的中兴气象。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神宗为此罢朝数日,赠上柱国,赐谥文忠,赐祭十六坛。可是还不到两年的时间,神宗皇帝便指斥他“怙宠行私,殊负圣恩”,“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明神宗实录》卷131,万历十年十二月戊戌),受到了抄家、夺爵等处罚,差一点就被开棺戮尸。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前贤时俊已经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答案。与张居正同时代的海瑞说他“工于谋国,拙于谋身”,这一结论得到了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同;后人也试图从神宗的心理入手,认为是长期受张居正的压抑而形成的逆反心理导致了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发生;也有学者从明代政治制度方面得出结论,认为张居正的当国就是皇权的失位,因此张居正的结局是任何有作为的政治家都不可避免的情形;也有从张居正自身性格寻找原因的,认为他胸襟狭小,任人唯亲才导致悲剧的发生。
本文拟从明代道德生活的角度来认识张居正的悲剧。所谓道德生活,就是人们在行为选择和价值评价过程中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道德氛围,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摆脱其影响的客观现实。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一个朝代,其社会生活开始发生一种全方位的、潜移默化的变革,而这种变革最集中、也最突出地表现在道德生活领域。如果我们尝试着用一个词来概括明代政治领域的道德生活,那恐怕就非“偏执”莫属。而张居正的悲剧就是这种“偏执”的产物。
一、对“祖宗家法”的偏执遵守
张居正死后,最先弹劾张居正的是陕西道御史杨四知,指责张居正在位期间“贪滥僭窃,招权树党,忘亲欺君,蔽主殃民”(《明神宗实录》卷131,万历十年十二月戊戌),等等。其实,类似这样的话,早在万历四年御史刘台就已经说过,他引用“祖宗家法”来指斥张居正的种种不端行为。所谓的“祖宗家法”,就是指太祖朱元璋所确定的各种章程。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宦官不得干政,洪武十七年,太祖铸造一块铁牌放置在宫门上,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明史·职官志四·宦官》)另外更加重要的一条就是废除丞相制度,“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
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明史·职官志一·内阁》)洪武十三年,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被诛以后,朱元璋就开始罢中书省,不再设置丞相。他振振有辞地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多贤相,然其中多小人,专权乱政。”[1](P70)由于自己的丞相有谋反的嫌疑,连带地将丞相制度也废除了,恐怕应该是“与臣下争意气而不与臣下争是非”[1](P82)的一种表现吧。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偏执”。
而且,自朱元璋开始,明代的皇帝是一个比一个偏执成祖朱棣以“清君侧”为名,从他侄子手中夺取了皇帝的宝座,已经为人们留下了诟病的口实,而他竟然不承认他侄子做了四年建文皇帝的事实,其偏执可见一斑;宣德皇帝自命不凡,陈祚以《大学衍义》劝令儒臣讲说,便大怒,谓:“竖儒薄朕未读《大学》,薄朕至此,不可不诛。”(《明史·陈祚传》)将陈祚一家关进大牢,终生不赦。正统皇帝的“夺门之变”比成祖的“靖难”更加令人不齿;正德皇帝离开皇宫而住“豹房”,在明代的皇帝中已经不算特别,可他自称“威武大将军”,则令人啼笑皆非;嘉靖皇帝信奉道教也无可厚非,可一意修真,专事斋醮,20多年不上朝则不能不令人齿冷;万历皇帝即位的
后30年,仍旧效法他的祖父,“不视朝,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奏章”,而且“中外缺官亦不补”;[1](270)天启皇帝自己是个文盲,无心也无力管理朝政,这不是他的过错,可他把朝政交给另一个文盲太监———魏忠贤,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张居正就是在明代政治的偏执已经发展到了极端的年代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尽管在他参政的嘉靖年间,没有权宦出现,但是嘉靖皇帝深居西苑,久不视朝,督抚大吏争献符瑞,内阁学士以青词邀宠,几届内阁首辅的明争暗斗却将明代政治的偏执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夏言、严嵩、徐阶、高拱,他们为了争夺首辅的权力已经使整个国家的政治充满了浓重的血腥气息。张居正能够坐上首辅的宝座虽然是得益于万历皇帝的登基,但其中带有戏剧性的过程已经给嗅觉敏锐的人们留下了太多的猜疑,如果他能够循规蹈矩地迎合当时沉迷、颓废的世风,那恐怕就会与绝大多数的首辅一样,善始善终。偏偏他是一个“进则为龙为光,退则为鸿为冥”(《张居正集·谢病别徐存斋相公》)的人,是一个高呼“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的人,怎么可能安于现状。因此,他上任伊始便开始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尊主权、课吏治、信赏罚、一号令。”(《明史·张居正传》)短短几年,便实现了“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太仓粟可支十年”(《明史·张居正传》)的中兴局面。明代官场中那种因循苟且的颓靡风气为之一新。
对于这一系列的变革,张居正一再强调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恢复“祖宗家法”,他也曾明确地对神宗表示:“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变更。”(《谢召见疏》)只是“惟日取我祖宗之法度而修明之”(《张居正集·书牍·答楚学道金省吾论学政》),但是,作为内阁首辅,如果按照祖训的规定,他是没有任何行政权力的,即便是为了恢复“祖宗家法”,也不在他的权限范围之中。这就是说,他的所作所为的确是违反了朱元璋的“家法”。
这里就存在一个如何认识“祖宗家法”的问题。自宣宗年间开始的内阁“票拟”和太监“批红”作法,表明“祖宗家法”在实际的政治运行过程中已经被打破了。英宗天顺元年,命吏部尚书李贤为文渊阁大学士,又开了内阁首辅的先河,这样,内阁的“票拟”权就掌握在首辅一个人的手中,而太监的“批红”权则一直把持在司礼监掌印太监及其手下的秉笔太监手中。可以看出,内阁首辅也好,秉笔太监也好,他们的权力其实就是建立在违反“祖宗家法”的基础之上的。这表明违反祖宗家法的既不是太监也不是首辅,而是皇帝。而对于内阁首辅来说,实际上是置身于二难困境之中,如果他遵循祖宗家法,便因为没有任何权力而无所事事,一任皇帝、太监的胡作非为,同时也就辜负了臣僚们所寄予的厚望;如果有所作为,便又无法严格地遵循祖宗家法,并给那些执着的儒家学者们留下了攻击的靶子,也让某些利益受损的官僚找到了打击他的借口。
很显然,能够破解这一迷局的关键人物是皇帝,如果他们能够像太祖一样的勤奋,收回秉笔太监的“批红”权,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即便不能收回,但能够从制度上赋予首辅以相权,使首辅可以名正言顺地总理朝政,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可明代的皇帝一代不如一代,既不敢从制度上突破太祖的“家法”,也不敢名正言顺地给首辅以实权,而他们自己对朝政却又没有任何兴趣,所以,明代的政治便一直处于这样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状态之中。而对于那位“中外想望风采”(《明史·张居正传》)的张居正来说,任何人都能够想象得到:无论他怎样选择,最终都难免道德方面的指责。
二、对道德理想的偏执追求
儒家思想发展到明代中叶,无论是理论的深度还是从内容的广度,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在张居正当权的时代,王阳明的心学已经取代了程朱理学成为儒家思想的主流。
本来,王阳明的心学是在理学内部生长出来的,是为了克服程朱理学“支离烦琐、帖括拘泥”的空疏学风而形成的,可是到了阳明后学那里,由于过分强调“求诸于心”、“率性而为”,又一次将儒学引入到了“大而无当”、“虚声窃誉”的空疏无用境地。而且,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阳明心学,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道德理想的执着追求。理学强调“穷天理、灭人欲”,试图通过极端的独断主义来实现儒家的道德理想;而阳明后学则采用极端的放任来实现心中的良知,这同样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而用理想的道德标准来衡量现实生活中的人,毫无疑问也是一种偏执。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他们对于张居正寄予了无限的期望。当时的吏部侍郎吴旺湖所说的话最具有代表性:“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可以看出,对于当时的士大夫和绝大多数的官僚们来说,政治活动的理想目标是实现孟子的“仁政”,已经没有了孔子“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的那种现实精神。如果政治家将治国的目标定位在“富国强兵”上,那就是等于放弃了儒家的道德理想。
从张居正柄政的十年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偏离儒家政治的理想追求,只不过他更多地从经世致用的立场来对待儒家的道德理想。“学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学;道不兼乎经济,不可以利用。”(《翰林院读书说》)在他看来,儒家道德理想不仅要培养道德完人,更重要的是要从自身的“修身”,推广至“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平天下”才是儒家政治的最高理想。而对于实现“平天下”这一道德理想的途径,张居正有他自己的理解:“孔子论政,开口便说‘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时’;周公《立政》:‘其克诘尔戎兵’,何尝不欲国之富且强哉?后世学术不明,高谈无实。剽窃仁义,谓之王道;才涉富强,便云霸术。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奚必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也。”(《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应该说,他的这段论述道出了问题的要害所在。因为“王道”也好,“霸道”也好,都是一种价值判断,其中涉及到一个评价标准的问题。如何确定这一标准,这是很多人都忽略了的。最早系统论述王道思想的是孟子,他将“仁政”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梁惠王上》)看成是实现“王道”的惟一途径,而判定是否“仁政“的标准在孟子这里有两个,即“不忍人之心”与“不忍人之政”。张居正明确地将评价标准设定为内在的“心”,即他所说的“在心不在迹”。张居正当政时期,正是阳明心学泛滥的时期,可他的批评者们则更多地将标准诉诸于外在的“迹”由于内在的“心”这一道德标准难以清晰、准确地加以判定,因此外在的“迹”,便成为了非常重要的指标。可以看出,张居正与他的批评者各自强调了其中的一点,而张居正所强调的这一标准由于说服力较弱而不利于自己。因此在他去世后遭到道德攻击就是在所难免的。那么,张居正悲剧的发生是否意味着他的政治措施就真的偏离了儒家的道德理想?
事实并非如此,这里还涉及到对“不忍人之政”的认识。孟子提出的“不忍人之心”,指的是“恻隐之心”,也可以说是“良心”、“仁心”、“道德心”。在“良心”的支配下实行的“不忍人之政”,指的是“德政”,也就是符合儒家道德原则、道德理念的政策,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实践中,就是那种以民为本、符合老百姓利益的政策。
作为一位现实的政治家,张居正不可能不顾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而一味地追求道德理想,但是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却是围绕着“安民”这一核心思想而展开的。这与儒家一贯倡导的“民本主义”是完全一致的。在改革的过程中,他一再强调:“致天下之道,莫急于安民;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请定面奖廉能仪注疏》)“法无古今,惟其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耳。时宜之,民安之,虽庸众之所建立,不可废也。戾于时,拂于民,虽圣哲之所创造,可无从也。”(《辛未会试程策二》)“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从这一角度来认识他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道德的意蕴就凸显出来了。
万历元年,针对“文卷委积,多致沉埋;干政之人,半在鬼录”等因循、敷衍的官风,上《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开始实行“考成法”。万历三年,针对大多数当时“以驰骛奔趋为良图,以剽窃渔猎为捷径。居常则德业无称,从仕则功能鲜效”的士风,上《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开始整顿学校教育;上《论边事疏》,整顿边备;同年也开始了整顿“驿递”(万历本《明会典》卷148)的行动;并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万历五年,开始实行大规模的清丈土地的活动。万历六年,启用潘季训治理“河槽”,获得成功。万历七年,开始实行禁“讲学”、毁书院的行动,毁全国书院64处。
万历九年,裁汰冗官一百六十余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万历十年二月,上《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主张免除积年逋赋一百余万两;四个月后,病逝。
在他短短十年的柄政生涯中,实行了如此规模宏大的利民政策,却仍然得不到信奉儒家思想的士大夫们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就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了。而导致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发生,一方面与批评者的自身利益得失有关,另一方面仍然是对道德理想的偏执追求在发生作用。从利益的方面说,清丈土地、“一条鞭法”等政策措施直接“损害”了土地占有者的身家利益;而整顿“驿递”、实行“考成法”也“侵犯”了官僚集团的某些“特权”;尤其是“毁书院”、“禁讲学”的政策的实行,得罪的就不仅仅是当权的官僚集团,而且得罪了几乎所有的读书人,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就可以说是得罪了整个社会。由此,孟森先生得出结论说:“当明末议论,于居正之有功国家,非士大夫切己之事,省记而持公议者较少,惟升沉进退之际,挟旧怨以图报复者为数较多。”[1](P261)从对道德理想的偏执追求方面说,当时的士大夫们要求他做一个道德完人,这方面集中地表现在对“夺情起复”的事件上。万历五年九月,张居正的父亲病故。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吏有丁忧制度,在明代,百官父母之丧,称丁忧。洪武八年诏百官闻父母丧,不待报即可奔丧,并解职守制三年。匿不举哀或不离职者,削职为民。守制期满,重新为官称为起复;丁忧期间如工作需要,皇帝可以“诏留视事”,称为“夺情”。张居正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上疏请求回籍守制却遭到了皇帝的“夺情”。尽管他一再上疏恳求,但仍然没有得到皇帝的批准。
面对这样一种状况,张居正又一次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不顾皇帝的旨意而回籍守制,就是对皇帝的不忠;如果遵从皇帝的“夺情”,就是对父亲的不孝。如何选择,任何人都难以抉断。坚持道德绝对主义的儒家士大夫看来,张居正应该义无返顾地回籍守制。因为即使没有了张居正,还有其他人同样为朝廷出力。可是在万历皇帝的眼里,张居正是一刻也离不开的,没有张居正在朝,那他就失去了心理上的依托,张居正十几年的教导将会付之东流。
其实,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形,也同样难以抉择。张居正自嘉靖三十六年销假回京之后,已经有十九年没有回江陵老家了,父亲去世了,无论是为父亲守制,还是探望老母,都有必要回去一趟。可是从皇帝的角度来说,也有比较充分的理由“夺情”。先皇托孤的遗命尚且不说,主要是皇帝尚未成年,而且大婚在即,作为首辅怎能轻言离开。更何况张居正柄政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都还在进行之中,没有了张居正的主持将难以为继。所以,除了“夺情起复”,没有更好的选择。即便这样,只要对立双方各让一步,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在明代,大学士丁忧被“夺情”,也是有例可循的成祖永乐六年的杨荣、宣宗宣德元年的金幼孜、四年八月的杨溥、景帝景泰四年的王文、宪宗成化二年的李贤,都曾夺情起复。五人之中,李贤与张居正一样也是首辅,而李贤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太平的时代,即使李贤丁忧,对朝政的影响也不会太大,远远不能与张居正所面对情形相比。可是,朝中官僚不肯退让,宁肯被廷杖也坚持要张居正回籍守制。其中很多人是张居正的门生、同乡,他们之所以坚持,更多的是用道德完人来期望张居正。如他的门生吴中行在请令居正回籍守制的奏疏中就说:“事系万古纲常,四方视听,惟今日无过举,然后后世无遗议,销变之道无逾此者。”(《明史·吴中行传》)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联名上疏也称:“夫社稷所重莫如纲常,而元辅大臣者,纲常之表也,纲常不顾,何社稷之能安?(《明史·艾穆传》)很显然,这是对儒家道德理想的一种偏执追求。他们不仅把这种偏执的道德追求当成自身的职责所在,而且利用这种偏执来增加个人的声望。正如孟森先生所说:“万历间言官封奏,抗直之声满天下。实则不达御前,矫激以取名者,于执政列卿诋毁无所不至,而并不得祸,徒腾布于听闻之间,使被论者愧愤求去,而无真是非可言。”[1](P267)在这样的道德氛围中,张居正的任何选择都会为他们留下攻击的借口。回过头来再看神宗皇帝,他要求张居正“夺情起复”,本来理由很充分,可他却不能平心静气地与臣僚们商量一个共同认可的方式,只是一味地坚持夺情,并对那些请令者动用廷杖,说他们“群奸小人,藐朕冲龄,忌惮元辅,乃借纲常之说,肆为排挤,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明神宗实录·万历五年十月丙午》)这同样是一种偏执,是明代皇帝特有的那种偏执。
三、对太监的偏执认识
阉人,不是中国的特产,但是宦官制度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杰作,并伴随着君主制度而不断发展。到了明代,“无论就宦官组织的严密、队伍的庞大,以及权势之重、危害之烈、作恶时间之长来说,都可以称得上是历代王朝之最。”[2](P14)由于宦官属于“刑余之人”,加之在历史上阉宦为害甚众,因此在传统社会中一直处于为人不齿的地位。但是由于宦官生活于皇宫之中并时时接近皇帝的特殊身份,所以在政治生活中往往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秦二世时期的赵高、后汉时期的“十常侍”、唐玄宗时期的高力士等等,都已经表明宦官干政所具有的巨大破坏作用。明太祖朱元璋有鉴于此,明令宦官不许干政,并铸了一块铁牌悬挂于宫门之上。可是在他的子孙的纵容下,有明一代,宦官操纵政治的情形是愈演愈烈。追本溯源,宣德皇帝赋予秉笔太监的“批红”权,应是明代宦官擅权乱政的开始。后来的皇帝对太祖的“家法”置若罔闻,而对这样的“放权”行为却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并成为政治生活的一种惯例。尽管自从正统皇帝时期的王振开始,直到熹宗时代的魏忠贤,权宦辈出,可是也没有哪一位皇帝能改变对宦官的依赖,可见明代皇帝对宦官的偏爱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而这样的结果,更加激发了官僚士大夫们的偏执情绪。从内心来说,他们非常瞧不起宦官,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又不得不与宦官打交道,并且还不能把关系搞得太僵,否则不只是难有作为,恐怕连性命都保不住。张居正悲剧的发生,就与宦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居正当朝的时候,司礼监掌印太监是冯保。史书记载,他是通过矫诏而任掌印,甚至说他与张居正相互勾结而受顾命,张居正也因此得冯保之力而排挤了高拱,坐上了首辅的位置。这种说法为攻击张居正的道德形象提供了直接的证据。但是仔细分析起来,疑问就出现了。据《明史》记载:“冯保,深州人。嘉靖中为司礼秉笔太监。隆庆元年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事。保善琴能书,帝……待之甚隆”(《明史·冯保传》)。可以看出,冯保是一个很有能力,并得到嘉靖、隆庆两位皇帝重用的太监。在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十年里,不仅与张居正配合得很好,实现了“宫府一体”,而且能够“束其子弟,不敢肆恶,都人亦称是”(《明史·冯保传》),没有发生权宦乱政的现象。张居正能够比较顺利地实行改革,与冯保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明史·冯保传》)同时他也能接受张居正的劝告,“裁抑其党,毋于六部事”(《明史·张居正传》)。甚至在张居正准备向神宗进献白莲和白燕时,他也能够并敢于劝阻:“主上冲年,不可以异物启玩好”(《明史·冯保传》)。这些都说明冯保是一个比较正直,深明大义的太监。但是,他与张居正之间的密切合作却引来了无数的猜忌,人们不相信司礼太监会支持首辅的改革,况且前任首辅还是在与冯保的争斗失败后去职的,因此他们之间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高拱的《病榻遗言》则为人们的猜忌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冯保与高拱的争斗由来已久。隆庆初年,司礼监掌印出现空缺,按照惯例应该由身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并提督东厂的冯保接任。高拱为了增加内阁首辅的权力,便设法抑制太监的“批红”权,他不愿意看到“善琴能书”的冯保掌握“批红”权这样的局面,因此极力推荐自己的同乡、御用监陈洪。这不仅违反了惯例,不合情理,而且负责营造事务的陈洪,文字能力较差,很难胜任司礼监掌印所具有的“批红”重任。很显然,高拱得罪了冯保。而在陈洪之后,高拱仍没有推荐冯保,又推荐尚膳监太监孟冲。由尚膳太监接任司礼太监,这在明代还没有过先例。因此,对冯保来说,这一次打击更加沉痛。痛失两次机会,冯保对于高拱自然是恨之入骨。可偏偏在隆庆皇帝死后不久,冯保就坐上了司礼监掌印这个位置,于是冯保与高拱的矛盾尖锐化了。高拱攻击冯保在神宗即位典礼上立于御座之旁是“欺皇上幼冲而慢肆无惮”,上《上新政五事疏》提出削弱司礼监权力,并指使御史劾奏冯保矫诏;冯保则在太后面前告状:“高先生云:‘十岁儿安能决事’”。(《明史·冯保传》)最后的结局自然是高拱被逐,而张居正则取代高拱成为新一任首辅。高拱下野以后,冯保又策划了一次“王大臣事件”欲置高拱于死地,但未如愿。
这样一次在明代已司空见惯的权力争斗,其中最直接的受益者张居正最终付出了最惨烈的代价。因为,人们怀疑冯保的所作所为都是与张居正合谋策划的,并且人们也都乐于相信高拱《病榻遗言》中所述及的事实,即冯保与张居正共同矫诏,并合谋驱逐他,最终为张居正出任首辅铺平道路。
对此,有的学者经过考证得出结论:张、冯二人不存在矫诏的可能;而张居正也并未卷入冯、高矛盾之中,对高拱被逐事先亦不知情。[3]本文认为这一“辩正”是可信的,因为有一点大家都很清楚,即作为这场争斗的主要受害者,高拱的叙述不能完全相信,其中存在着由于痛恨冯保、忌妒张居正而恶意中伤的可能性。更何况《病榻遗言》的作者是否就是高拱本人也值得怀疑。[4](P35)
其实,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除掉当事人各自的利益打算之外,情绪、态度上的偏执又一次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首先,高拱对于太监的偏见导致了自身被逐的结局。明代太监的“批红”权,虽然是违反祖宗家法而赋予的,但自宣德皇帝以来已成惯例,难以遽然改变。更何况小皇帝刚刚即位,身边没有一个信得过、又有能力处理朝政的人,他这个皇帝怎么能做下去而且作为一位历事三朝三十余年的老臣,高拱怎能不明白:既然皇权旁落不可避免,与其交给阁臣,还不如交给太监,这是明代皇帝们心照不宣的事情。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其公开地与司礼太监作对,倒不如引导他们忠心地为朝廷服务。可他偏偏对百余年来相沿成习的事实视而不见,企图扩大内阁首辅的权力,除了偏执就很难解释。其次,以讹传讹的官僚士大夫们,他们以对太监的偏见作为攻击张居正的借口。太监从事固然是皇宫贱役,但在明代则不尽然,宣德皇帝开设的“内书房”,使很多太监不仅识文断字,文笔优秀的甚至可以润色大学士的文章。而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们从事的工作与外朝大臣们没有任何区别,仅仅因为他们是“刑余之人”就从道德、能力等方面否定了他们,同样是一种偏执。虽然有很多太监干权乱政,但不等于所有的太监都是一样的,郑和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因为冯保是太监,就一定是冯保错了,即便冯保有问题,那也不等于高拱就没有问题,而把张居正也牵扯进来就更没有道理了。
可以想见,以“勇于任事”而著称的张居正,不可避免地也有他的偏执之处,他曾经不无自负地说过:“吾平生在师心,不蕲人知,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况欲侈恩席宠以夸耀流俗乎?”(《答湖广巡按朱谨吾辞建亭》)二十年前曾有一弘愿,“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欢喜施与,况诋毁而已乎?”(《答吴尧山言弘愿济世》)在一种偏执的政治生活中,用这样一种偏执的精神来推行社会改革,尤其是涉及到官僚士大夫切身利益的改革,张居正悲剧的发生就是意料之中的了。
参考文献:
[1] 孟森.明史讲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 卫建林.明代宦官政治[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
[3] 荣真.隆庆末张居正冯保矫诏辨正.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5):40-45.
[4]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