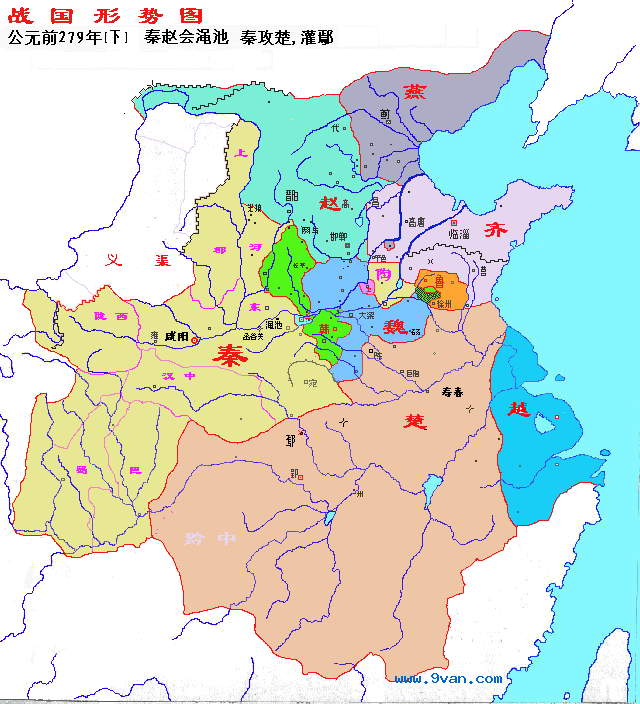人性论、君子小人与治国之道——论《韩非子》的内在逻辑
一
迄今为止,在对《韩非子》的研究中,存在着许多争议,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韩非是否性恶论者?韩非的道德观是否属于非道德主义?《韩非子》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是势治、法治还是术治?秦朝的灭亡是否意味着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治国思想的彻底失败?等等学者们对《韩非子》的认识之所以存在上述诸多分歧,除了各人理解上的偏差,也与《韩非子》一书某些具体论述中存在的自相矛盾有关。《韩非子》是由韩非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所写的几十篇论文编纂而成,书中论述确实存在一些前后不一及矛盾之处。这致使后世学者在论述《韩非子》时,大多采取“六经注我”的方式,执其一端以阐己说;有的则干脆把《韩非子》中一些与自己所理解的韩非思想宗旨不合的篇章列为他人之作。以致古往今来,治《韩非子》者颇众,而真正能为众人接受的论述寥寥。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对《韩非子》的认识和评价只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呢?我认为不是的。因为当我们不拘执于《韩非子》关于某一问题论述时的只言片语,而深入到对《韩非子》内在逻辑的把握时,许多矛盾与疑惑便可迎刃而解。
那么,《韩非子》一书的内在逻辑又是什么呢?本人不揣冒昧地认为:以人性论为基础,以对君子小人的特点和现状的把握为中介,以对治国之道的具体论述为主体内容,就是《韩非子》的内在逻辑。
把人性论看作是韩非关于治国之道的基础,这似乎已是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而对君子小人的论述在《韩非子》中并不占有重要篇幅,它怎么竟会成为《韩非子》内在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呢?
为了较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在此有必要简述一下先秦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内在逻辑。因为《韩非子》几乎是在与儒家德治学说的交锋中著述而成的,儒家思想的内在逻辑可以帮助我们看出《韩非子》思想的清晰脉络。
详细地研究以《论语》、《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不外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仁、仁政、礼治的思想,二是关于君子小人的丰富论述,三是关于人性善、恶的学说。其实,这三个方面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而且,进一步的研究将使我们发现,儒家的上述三个方面的思想并不是互不相干的,而是互相联结,构成了儒家思想严密的内在逻辑:人性论是君子小人之分的基础,对君子小人的深刻认识和严格区分又是儒家治国之道的依据。具体说来,就是儒家认为:每个人都有先天相同的本性,这一本性决定了人在后天为善为恶的可能性;通过后天严格的道德教化,人人都可成为君子;但在现实社会中,由于所受教育程度不同,君子与小人并存,所以最好的治国之道,就是用仁义道德培养人,即孔子所谓的“道之以德”(《论语·为政》),最终使人人都成为道德君子。
在儒家看来,在一个人人都是君子的社会里,就会充满和睦、安宁和欢乐,就不会有争斗、欺诈和暴虐。因此,无论孔子、孟子还是荀子,都以把全体百姓培养成君子作为他们最崇高的目标,这正如《礼记·大学》中所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他们确定君子的标准,划分出人的不同修养层次,无非是希望人人都能照此实行,最终成为君子。
孔、孟、荀确定的这个目标,虽然被当时的许多人看成是迂阔而不切实际的,但孔、孟、荀却认为是很容易实现的。因为按照他们的逻辑: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存在着君子,而且,除了极个别者,大多数的君子都是通过后天培养出来的;既然君子是可以培养的,“君子国”的状况又是如此的令人神往,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为实现“君子国”的理想而奋斗呢?
当然,他们也承认,在现实生活中,君子的影响力仍然有限,社会上充斥着小人,但不能据此就放弃通过施仁义道德把小人培养成君子的目标。孟子曾以“杯水车薪”的例子来加以说明:“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因为在他们看来,之所以会造成目前社会这种混乱的局面,完全是由于统治者没有认识到培养君子的重要性而造成的,一旦最高统治者认识到培养君子的重要性,并以身作则,加以实施,那么“君子国”的产生将是极为容易的事:“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孟子·离娄》)而君主以德治国的影响力之所以会如此之大,是因为道德的推行,将会像春风的流行一样迅捷,即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当然,我们说儒家提倡德治,只是从儒家最根本的治国方略的意义上来说的,因为儒家并没有否认法治的作用,孟子就明确说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但从德治与法治的地位来说,儒家是重德治而轻法治的。因为儒家认为道德完善是人生最崇高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光靠法治是不行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论语·为政》)高尚的道德只有靠道德手段来建立,所以德治才是最重要的。
二
以上述儒家思想的内在逻辑为参照,我们可以把《韩非子》的内在逻辑概述如下:人人都有好利恶害的自然天性,这一天性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必然是趋利避害的,在一个秩序混乱、社会动荡的环境中,除了极少数的君子,人人都把个人的利益看成高于一切,这是当今社会小人充斥的重要原因;基于这种现实,治国的方略只能根据小人的特性来制定,只有通过严格的法治才能使小人改恶从善,而德治的方法不仅无益于改造小人,甚至会使仅有的君子也成为小人。进一步说,在韩非看来,理想社会的实现,与其用儒家主要依靠不成文的习惯原则和难以把握的特殊性、灵活性(“权”)为手段,不如以用成文的规范形式、追求具有普遍确定的平等和一致的手段——法更为有效。因此,韩非认为,人们的道德行为不能依靠道德手段去建立,法治才是确立人们道德行为的重要手段,君主只要实施严格的法治,很快就能达到“君子与小人俱正,盗跖与曾、史俱廉”(《韩非子·守道》,以下称引该书,只注篇名)、国富民强的理想境界。
由上述可以看出,儒法两家的本质区别既不在人性论,也不在对现实社会与理想社会的理解上,而是在对达到理想社会所用手段的选择上。
下面,我们对《韩非子》的内在逻辑展开系统的论述。
韩非人性论的特点是简洁明了:“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外储说左上》),“父母之于子女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六反》),“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二柄》);并由此直接推出治国之道:“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八经》),“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二柄》)。
由于韩非人性论的上述特点,导致后世学者在对韩非思想的理解上,存在两个误区。一是一些学者认为韩非是性恶论者。因为既然韩非认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由自私自利之心必然产生争夺,这种人性就不是善的,所以韩非当然是性恶论者。二是把《韩非子》的内在思想逻辑简单理解为以人性论为基础,以治国之道为具体内容,从而忽视了韩非关于君子小人的丰富思想,在对韩非思想的理解上走向简单化,并使韩非的道德论长期得不到正确理解。
其实,说韩非是性恶论者只是后世学者所贴的标签,因为翻检《韩非子》全书,确实没有关于人性恶的明确说法(当然也没有关于人性善的说法)。后世一些学者之所以硬要认定韩非是性恶论者,无非是为了给韩非提倡严刑峻法找到更确切有力的依据。其实在我看来,性善论与性恶论的真正价值和实质区别并不在于谁在人性问题上说出了更多的真理,因为无论孟子还是荀子,都是把其思想的重点放在对人的后天教化中的。一些思想家之所以要把人性作善恶的区别,很大程度上是适应了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习惯:对一个变成坏人的好人充满同情之心而对一个变成好人的坏人充满防范之心。这也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来理解为什么在治国之道上孟子提倡仁政而荀子则侧重于礼治。韩非对人性不作善恶的界定,这正是他理论的平实明白之处:从人性的自私自利和所处时代的特点出发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治国之道,不是更直接更容易吗?为什么非要加上人性善恶的标签呢?孔子之“罕言性与天道”,并对人性不作善恶的区分,何尝就不是出于此种考虑呢?
从韩非的人性论和赏罚论,似乎推导不出现实社会中有道德的存在。因为既然人性是自私自利的,治国之道是根据人性的自私特点制定的刑赏法则,怎么还会有道德存在和生长的空间呢?许多学者正是由此认定韩非是非道德主义者。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我认为,要对这个问题作彻底的澄清,只有从韩非关于君子与小人的论述入手。
把社会上的人群划分为君子与小人两大类,是先秦思想家的普遍做法。虽然各家对君子小人的理解和提法不尽相同,但大体说来,有一点是一致的,即认为君子是有道德的人,重义轻利的人,而小人则是不讲道德的人,轻义重利的人。从韩非关于君子小人的论述来看,他基本上沿用了这一传统观点。
韩非关于君子与小人的论述分散在《韩非子》的各个篇章中,但综合起来,还是可以看出他关于君子小人的思想是极为系统的。首先,他认为君子小人是一种客观存在。如在《用人》中,韩非明确指出君主对君子和小人应采取不同的态度,否则,就会给自己带来祸害:君主“喜则誉小人,贤不肖俱赏;怒则毁君子,使伯夷与盗跖俱辱;故臣有叛主”。其次,他认为有无道德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在《难二》中,韩非为了批驳“夫言语辨,听之说,不度于义者,谓之窕言”的说法,就是以君子小人的区别为武器,说明此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因为“听者,非小人,则君子也。小人无义,必不能度之义也;君子度之义,必不肯说也”。而在《解老》中,韩非更是明确认为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于能否守住真诚:“真者,慎之固也……修身者,以此别君子小人。”在《韩非子》一书中,类似的论述是非常多的。
既然君子是客观存在的,那么,这些君子又是怎么来的呢?纵观《韩非子》全书,可以发现,君子的来源不外两个,一个是天生的,如《难势》中说:“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尧、舜的出现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只能理解为天生的;二是后天培养的,如《安危》篇中说:“治世,使人乐生于为是,爱身于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可见,在韩非看来,在一个政治清明的社会中,是可以培养出大批君子的。
韩非虽然承认社会上存在君子,但他慨叹说,这些君子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五蠹》),“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同上)。
君主治国,针对的是全体国民,而君子只占全体国民的极少部分,所以,韩非指出,治国之道不能按君子的特点来制定,以君子之道治国只能是一种迂阔而不切实际的空想:“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五蠹》)。另外,以君子之道治国也会给社会的治理带来祸患:“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同上)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韩非对儒家的德治主张进行了全方位的批驳,并在此过程中明确阐述了自己的法治主张。
一是认为德治主张不符合时代的需要。韩非认为,实行德治,只是远古时代的事,在当今的大争之时,已明显过时了:“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非圣人之治也。”(《八说》)关于韩非所处时代的特点,《史记·六国表序》中有这样的描述:“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可见,在这样一个人们道德普遍沦丧的时代,再去提倡把道德感化作为最重要的治国手段,无疑是太可笑了。
二是德治见效缓慢(甚至无效)而法治见效快捷。在这个问题上,韩非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舜用了三年时间、通过身体力行治理地方事务的例子,说明德治的劳而功缓:“舜救败,期年已一过,三年已三过。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难一》)而法治则不然:“赏罚,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赏,弗中程者诛。’令朝至暮变,暮至朝变,十日而海内毕矣,奚待期年?”(同上)另一个是不肖之子无法用母爱师教加以改变,执法官吏一到,立即恐惧变节的例子:“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五蠹》)
三是德治之道难以实行。按照儒家的说法,德治必待尧、舜那样的有道之君以身作则,加以推行,而在韩非看来,尧、舜“千世而一出”,社会岂不是要长久处于动乱之中:“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难势》)而且,即使从具体实行来说,德治主张什么事都要君主以身作则,也是不切实际的:“且夫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难一》)所以,在韩非看来,德治之道完全是不切实际的言论。四是德治将给社会带来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首先是利奸人而害良民:“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盗贼者伤良民。今缓刑罚,行宽惠,是利奸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为治也。”(《难二》)其次是会在用人政策上造成自相矛盾:“今人主以其清洁也进之,以其不适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誉之,以其不听从也废之。民惧,中立而不知所由,此圣人之所为泣也。”(《外储说右下》)第三是会带来亡国之祸:“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爱也。夫有施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则暴乱者不止。国有无功得赏者,则民不外务当敌斩首,内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货财事富贵,为私善立名誉以取尊官厚禄。故奸私之臣愈众,而暴乱之徒愈胜,不亡何待?”(《奸劫弑臣》)而如果实行了法治,上述种种弊端就可彻底避免:“明赏设利以劝之,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严刑重罚以禁之,使民以罪诛而不以爱惠免。是以无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义惠爱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同上)
接下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韩非不光反对德治,而且反对治国时德治与法治并重。长期以来,因为受汉初思想的影响,人们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是只重法治,不重德治,所以恩威并用、霸王道杂之、德治与法治并重似乎就成了有效的统御术的代名词,其实这恰恰是韩非所极力反对的。在韩非看来,采用什么样的治国之道,是用法治还是德治,完全是根据国家所处的时代环境和面临的中心任务来确定的,那种治国时对什么都并重的做法,貌似公允合理,其实是治国之道的最大祸害。对此,韩非给我们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秦昭王生病,百姓们纷纷买牛为他祈祷,秦昭王不仅不因此感谢百姓,反而处罚了地方官。理由是:“夫非令而擅祷,是爱寡人也。夫爱寡人,寡人亦且改变而心与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乱亡之道也。”(《外储说右下》)韩非对秦昭王不以德乱法的做法极为赞赏。正是沿着这一思路,韩非称法治与德治并重的国家为“无常之国”:“行义示,则主威分;慈仁听,则法制毁。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势卑下,故下肆很触而荣于轻君之俗,则主威分。民以法难犯上,而上以法挠慈仁,故下明爱施而务赇纹之政,是以法令隳。尊私行以贰主威,行赇纹以疑法;听之则乱治,不听则谤主,故君轻乎位而法乱于官,此之谓无常之国。”(《八经》)而“无常之国”必亡。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韩非提出了他的法治高于一切的主张:“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五蠹》)有的论者把此段话当作韩非的极端专制主义的代表性言论加以抨击,其实是由望文生义造成的假如我们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到战国晚期的大规模兼并局面之中就会发现在力强者存、力弱者亡的严峻形势面前,韩非的这一论述是多么的振聋发聩,多么的具有现实价值!
但是,韩非反对德治、反对德治与法治并重的治国方略,却并没有就此反对一切道德的价值和作用,而是认为,当今社会的一切道德行为,都是君主厉行法治的结果;而一切不道德的行为,都是因为法治不严或行德治造成的。所以,在韩非看来,在现实社会中,人们的道德行为是法治的结果,而不是通过道德教化的手段造成的。在《饰邪》中,韩非提出,人人都有为公和为私两种倾向,如果施行法治的明主在上,人们就会去私心,求公利:“人臣有私心,有公义。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则人臣去私心行公义;乱主在上,则人臣去公义行私心。”而且,如果君主不采用法治,那么,即使是本来有道德的人也有可能变成小人:“人主离法失人,则危于伯夷不妄取,而不免于田成、盗跖之取可也。”(《守道》)
正是基于上述逻辑,韩非描绘了因实行严格的法治后社会所达到的道德高尚的美妙境界:“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法……善之生如春,恶之死如秋,故民劝极力而乐尽情……守道者皆怀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节。”(《守道》)
韩非认为法治在争于气力的乱世是建立道德行为的惟一手段,这一观点是极具启发意义的。当然,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中外学者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迄今并无众所公认的定说。但有一点学界的看法是较为一致的:道德与法律涉及的是社会生活中的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虽有互相影响的地方,但绝不能互相取代。许多论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批判韩非重法不重德,把社会生活简单化,看不到道德在调节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其实,对于这个观点,是应作具体分析的。
为法律和道德有不同的管辖范围,这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真理。对于这一点,韩非并没有反对。因为韩非并没有否定道德的价值和作用,他甚至认为在一个人人都是君子的社会,是用不着什么法治的,人们的道德行为将对调节社会生活起到巨大的作用:“尽如比干,则上不失,下不亡。”(《安危》)但是,当社会进入乱世之时,欺诈盛行,暴虐成风,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来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便失去了它的制约作用;不仅如此,连法律也失去了往日的威严,而成为人们轻易冒犯的领域。因此,如果在此时再去恪守什么法律与道德的严格分野,便是一种极为荒唐的行为。统治者要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唯一可以使用的只有一个手段:乱世用重典!不仅要加强法律的惩戒力度,甚至要把原来由道德管辖的领域纳入法律管辖的范围。韩非之重法治,反对德治,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的。
其次,法律与道德的分野本来就不是十分清晰的。从人们普遍认同的关于道德的两个重要特征来看:道德行为必须出自内心自觉,道德行为是靠社会舆论等非强制手段来维系的。这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因为所谓内心自觉,是指不受外力强制,但这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韩非就明确说过:“夫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六反》)事实上,人们之所以选择道德行为,是接受长期教化的结果,而教化本身就是带有强制性的。而且,法律手段也会造成人们内心的道德自觉。当法律的管辖范围囊括了道德领域时,久而久之,人们也会发自内心地不去触犯法律,而在这发自内心地不去触犯法律的行为中,有一部分就转化成了道德行为。《商君书》把这一特点称为“心断”,即一切行为都是以人们的内心为衡量标准,而不再需要任何外在的法律强制,它说,“故有道之国,治不从君,民不从官”,而“一于心断”。至于道德的以社会舆论等非强制手段来维系的特点,我认为它与法律的靠国家机器强制的特点只有量上的区别,而并无本质的区别。因为社会舆论的褒贬作用与国家强制机器的赏罚一样,都是能给人们的利益带来切实影响的行为,只是程度不同罢了。所以我认为韩非在道德与法治关系上的论述给我们的重要启迪是:一个社会重德治还是重法治,关键是要看采用哪种手段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确实能用道德手段来解决的问题,当然没有必要诉诸法律;同理,那些事实证明用道德手段已经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不要再天真地去期待什么国民道德素质的普遍提高,而应果断地诉诸法律!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得不再次佩服韩非的真知灼见:“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故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世知,维之以刑,则从。”(《心度》)因此,我常常禁不住纳闷:即使从纯粹实用的角度来看,法家思想对我们现实社会的借鉴作用也远远超过儒家,为什么鼓吹新儒家者甚众,而鼓吹新法家者竟无一人?
至此,我们有必要回头来看一下关于韩非是非道德主义者的观点。此观点在目前关于《韩非子》的研究中有较大影响,认同者颇众。然而我认为,此观点完全是偏执于《韩非子》中的只言片语造成的。因为根据人们对非道德主义的定义:“非道德主义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伦理思想,不仅否定道德的功能与作用,更重要的还在于否定道德自身”(见《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7月第4期《评韩非的非道德主义思想》一文),我们只要找出一个反证,此观点便不攻自破。而从上面韩非关于道德问题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此类反证简直是数不胜数。因此,此处我只是引用韩非对自己舍身取义行为的解释来作为对该问题的结笔:“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问田》)
三
在文章的最后,将谈一下对《韩非子》一书的评价问题。目前学界关于《韩非子》的较为一致的评价有这样三个方面:一是认为《韩非子》只重法治,不重德治,是其致命的缺陷;二是认为秦王朝的灭亡意味着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治思想的破产和失败;三是认为自汉以后,《韩非子》中以阴酷著称的术治思想被历代封建帝王所吸收,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治国思想中阳儒阴法的独特局面,因此,《韩非子》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于第一个方面,上文对此已有较多展开,就不再赘述了。至于第二个方面,认为秦王朝的灭亡意味着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治思想的破产,我认为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仔细分析秦王朝灭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昏君当道, 2.奸臣弄权, 3.徭役繁多, 4.严刑峻法, 5.实施暴政。这五个方面,与《韩非子》中的思想大多是相违背的。
首先,防奸术是《韩非子》术治思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韩非在《说疑》中说:“孽有拟适之子,配有拟妻之妾,廷有拟相之臣,臣有拟主之宠,此四者,国之所危也。”可谓直指胡亥和赵高。而类似的论述在《韩非子》中简直比比皆是。
其次,韩非明确反对徭役繁多:“徭役多,则民苦;民苦,则权势起;权势起,则复除重;复除重,则贵人富。苦民以富贵人,起势以藉人臣,非天下长利也。”(《备内》)
第三,提倡严刑峻法,确实是韩非思想的一个核心。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韩非之提倡严刑峻法,是针对“当今争于气力”的兼并局面而言的,他明确提出在不同的时期要运用不同的治国方法。那种认为韩非应为秦王朝实施严刑峻法承担责任的观点,事实上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即使在大一统的秦王朝建立后,韩非也会主张严刑峻法。这是否太过武断了呢?
第四,韩非明确地反对暴政:“暴者,心毅而易诛也……心毅,则憎心见于下;易诛,则妄杀加于人……憎心见,则下怨其上;妄诛,则民将背叛……暴人在位,则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乱心生……亡国者也。”(《八说》)因此,把《韩非子》与秦王朝的灭亡直接联系起来的做法是不适当的。
关于第三个方面的评价,我认为《韩非子》中的术治思想充满了血腥、狡诈和残忍,确实是整部《韩非子》中最阴暗、最应抛弃的部分。但至于这些思想被后世统治者发挥运用,则不能主要归咎于《韩非子》。
韩非的术治思想,植根于他对君臣关系的认识。在韩非看来,君臣之间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故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饰邪》)既然如此,如何防范臣下的篡夺行为,就成了君主的重要任务。因此,韩非在倡导法治的同时,也提出了专门针对臣下的术治主张:“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定法》)把术治作为法治的不可或缺的补充,是韩非思想逻辑的必然结果。因为在韩非所处的时代,君权是高于一切的,以法治作为普遍准则,必然涉及对君主权力的限定问题,这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时,如何任用、考察臣子并不是运用法治就能解决的。因为那时候的国家,是君主的国家,而不是人民的国家;君主的地位,主要是靠世袭得来的,而不是靠民意产生的。这就决定了人民对国家政策特别是政府官员的任用既没有发言权,更没有监督权,因此,君主只能采取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办法,所以只好凭势运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后世对《韩非子》的不恰当的认识,术治思想这一《韩非子》中最阴暗的部分被以“阳儒阴法”的方式长期保存了下来,而《韩非子》中闪耀着真理光芒的法治思想、关于法治与道德关系的精辟论述,却被轻率地抛弃了。这个责任,当然应归于后世的统治者和思想家们。
我一直认为,研究古人思想,不能只看古人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要看古人为什么这么说,他们是在什么环境下、针对什么情况这么说的。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到古人思想的内在逻辑,去把握古人思想的实质。否则,不是对古人思想作歪曲的理解,就是拘执于古人思想中的只言片语,去作永远也争执不清的无谓争论。
所以,研究《韩非子》,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它是针对战国晚期“争于气力”的大规模的兼并局面立论的。中华民族最近一百多年来被瓜分、欺辱的历史告诉全体中国人民一个真理:落后就要挨打!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教训,我们来重温《韩非子》的法治思想,研究它的内在思想逻辑,并试图对它进行重新评价,这不是很有意义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