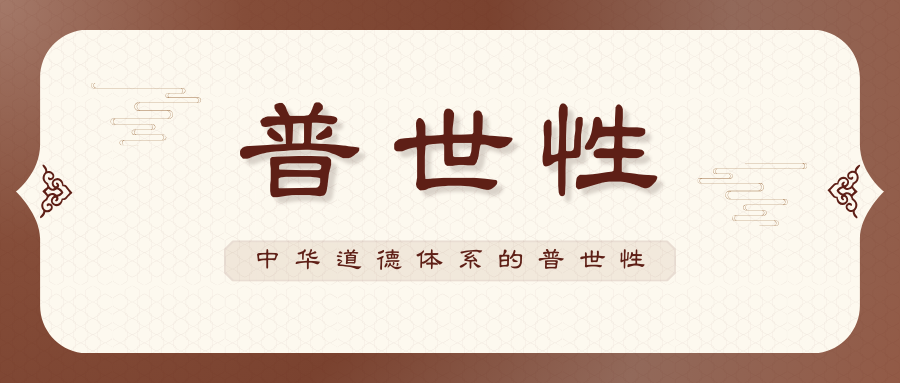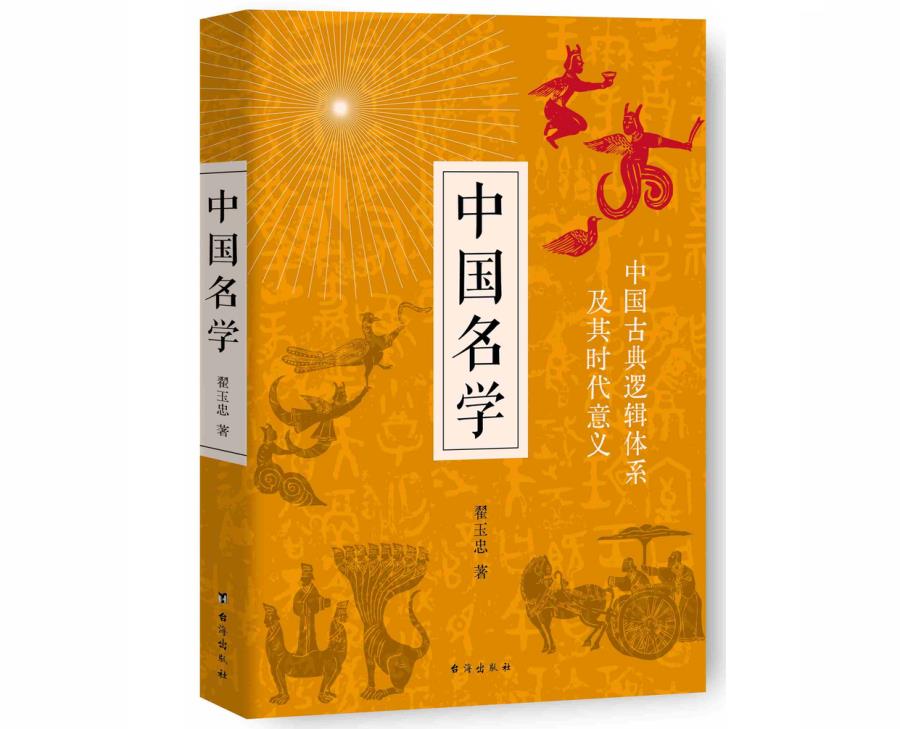何谓名教?简单说,就是“以名为教”,以名分、社会责任为教化的礼教和礼义之道。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浓厚宗教传统的文化中,名教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所谓“上士教之以道,中士训之以德,下士拘之以神”,若一个社会整体上不能用神道约束,则只能训之以德,故名教亦有礼教、德教之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海燕在《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一文中写道:“名教的含义也近于‘德教’‘王教’‘风教’‘儒教’。称为‘礼教’,系侧重于礼仪有助教化;称‘德教’是取其道德之义,称‘王教’是由于王权介入教化,称‘风教’是着眼于风俗与教化的联系,称‘儒教’是因名教为儒家所标榜。至于称之为‘名教’,则是强调以名为教。”【1】 庞朴先生进一步指出:“所谓‘以名为教’,就是把适合某种需要的观念和规范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以此来进行教化。”【2】 北齐文学家颜之推(531—约595年)《颜氏家训·名实》反驳了一些人认为人死如灯灭,不重名声的观点,谈到名教劝善戒恶的道德教化功能时他说: 名教是为了劝勉大家。劝勉人们树立好的名声,就可以指望他们有与名声相符的实际行动。况且劝勉人们向伯夷学习,成千上万的人就可以树立起清廉风气了;劝勉人们向季札学习,成千上万的人就可以树立起仁爱风气了;劝勉人们向柳下惠学习,成千上万的人就可以树立起忠贞风气了;劝勉人们向史鱼学习,成千上万的人就可以树立起正直风气了。所以圣人希望世上人才像鱼鳞凤翼一样众多又各有所长,不断出现,这难道不伟大吗?四海之内,百姓众庶,都爱慕名声,应该据此引导他们达到美好的境界。或许还可以这样说:祖先们的美好声誉,好像是子孙们的礼服和大厦,从古到今得到其庇荫的人够多了。广修善事,树名声,好像建筑房屋,栽种果树,活着时能得到其好处,死后可泽及后人。【3】 北宋范仲淹谈到名教的社会功能时也说:“我先王以名为教,使天下自劝。汤解网,文王葬枯骨,天下诸侯闻而归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钩以邀文王,夷齐饿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国以求行道,是圣贤之流,无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书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贬之,使后世君臣爱令名而劝,畏恶名而慎矣。”(《范文正公集·近名论》) “名教”一词较早出现在《管子·山至数》,上面引齐桓公言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诸侯宾服,名教通于天下。”至魏晋,该词尤为流行。当时学人将名教与自然秩序协调起来,提出名教出于自然之情,本乎自然之性。比如东晋史学家袁宏(约328—约376)说: 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夫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失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后汉纪·卷二十六·献帝初平二年》) “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强调上下级和父子间的社会责任。《论语·颜渊篇第十二》记载,齐景公(前547年—前490年在位)曾问孔子治理国家的方略,孔子认为名分的确定最为重要——做君主的要像君的样子,做臣子的要像臣的样子,做父亲的要像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像儿子的样子。否则,只能是社会大乱。用齐景公的话说,就算有粮食也吃不上了。文中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今人将君臣、父子,以及后来三纲中的夫妇理解为“封建等级秩序”,这过于简单化;相反,它如实地反映了社会秩序中人际间复杂的互相依存关系,是一切文明社会的基础,所以更具有普世性。《管子》中的诠释更为清楚,《管子·匡第二十》引管仲言曰:“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管子·形势第二》中又说:“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管子·形势解第六十四》是对《管子·形势第二》的解说,从中我们看到,三纲表示社会中平等互系的关系,目的是维系社会整体和谐。上面说:“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义以正其臣,则臣不知于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则臣不臣。’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义以教其子而整齐之,则子不知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则子不子。’君臣亲,上下和,万民辑,故主有令则民行之,上有禁则民不犯。君臣不亲,上下不和,万民不辑,故令则不行,禁则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西汉董仲舒用阴阳解释人伦的基础架构三纲,所言极为精当。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开篇指出,“凡物必有合”,这里的“合”是相互配合,协调统一之意。文章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 先秦儒家论名教,名位、职分与德目并重,这就是郭店楚简《六德》中的“六位”“六职”“六德”。六位即:夫、妇、父、子、君、臣;对应的六职是:夫之率人、妇之从人、父之教人、子之受人、君之使人、臣之事人;六德分别是:夫之智、妇之信、父之圣、子之仁、君之义、臣之忠——后世儒家将之简单的总结为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忽略了职分,这不仅模糊了名教的名学基础,也使礼教逐步退化为老生常谈的道德说教。 20多年前笔者在唐山老家从事教育工作时,遇到一个十分捣蛋的学生,父母对其疼爱有加,总认为自己的孩子没有什么大问题。每次我见到那位学生的父亲,要他好好管束孩子时,这位老实的父亲总是说:“现在我养他,将来他养我,孩子树大自直。”后来我回老家,听说这位父亲自杀了。我大为吃惊,问其原因。原来其子将父亲做生意的钱偷走了,这位父亲怎么也想不开,自己养活儿子,儿子怎还偷自己,最后干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父之教人,乃天职。正名定分,按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完成自己份内之事,在儒家同在法家一样具有基础地位。 名教真义如此重要!不幸的是,20世纪初,国人面对深重的生存危机,在儒家不能提供足够思想资源的情势下,新文化运动主将们将矛头直指儒家礼教,在“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这类口号声中,适合中国人特点、符合自然秩序的名教被弃如敝履。近百年后,由于没有宗教能够替代名教的社会教化功能,当代中国物欲横流,近乎成为一个道德塌陷区。 是的,君主时代结束了,君臣之伦不复存在,但上下级关系不会消失,上下之义仍要坚持,此为情之不可废者。近人齐树楷早在1923年就论证说:“君主民主,时代已更,不但改步改玉(指死者身份改变,安葬礼数也应变更——笔者注),枝叶之名已变,即伦纪之数,纲常之教,人乃欲牵一而动之。君主去而以为君臣伦废,其他各伦,人之所以生者,几至根本皆摇。不知古圣人创制之源,有因乎势者,有因乎情者。势之不存,并举其因乎情者而易之,其不至治丝而棼(棼,音fén,纷乱。治丝而棼指理丝不找头绪越理越乱,比喻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正确,使问题更加复杂——笔者注)者,未之有也。”【4】 不懂得先圣立教根本,治丝而棼,这是上个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对待名教的方式,结果则是道德的普遍缺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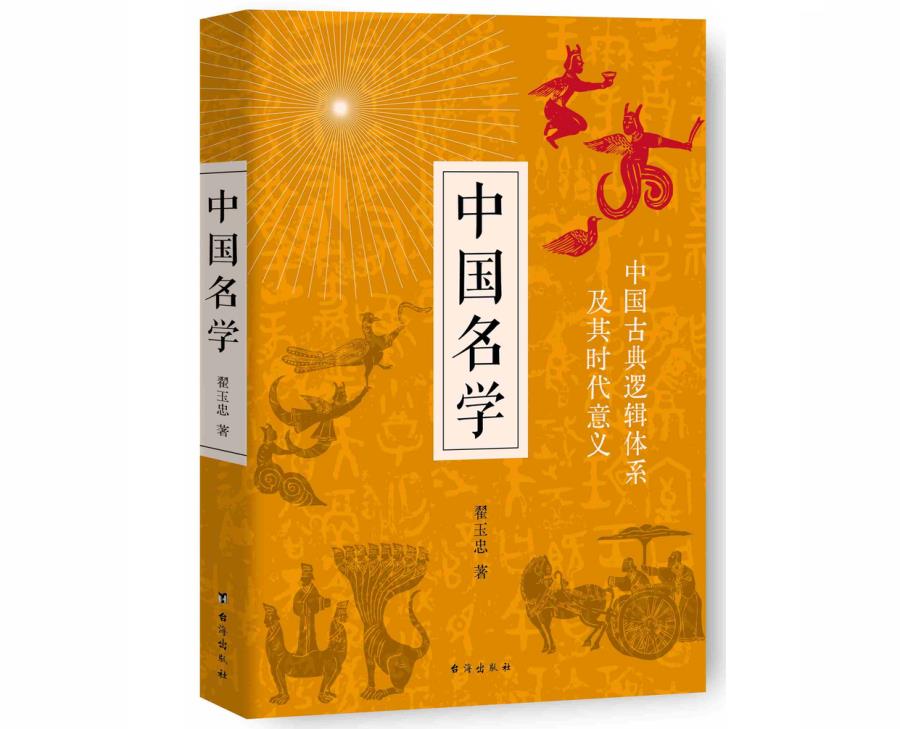
(选自《中国名学:中国古典逻辑体系及其时代意义》,该书可在京东、当当上买到;支持我们,欲购作者签名版请加微信:zhai20050718) 注释: 【1】张海燕:《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载《学人》第11辑,1997年。 【2】庞朴:《中国的名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年,第6页。 【3】原文:或问曰:“夫神灭形消,遗声余价,亦犹蝉壳蛇皮,兽迒鸟迹耳,何预于死者,而圣人以为名教乎?”对曰:“劝也,劝其立名,则获其实。且劝一伯夷,而千万人立清风矣;劝一季札,而千万人立仁风矣;劝一柳下惠,而千万人立贞风矣;劝一史鱼,而千万人立直风矣。故圣人欲其鱼鳞凤翼,杂沓参差,不绝于世,岂不弘哉?四海悠悠,皆慕名者,盖因其情而致其善耳。抑又论之,祖考之嘉名美誉,亦子孙之冕服墙宇也,自古及今,获其庇荫者亦众矣。夫修善立名者,亦犹筑室树果,生则获其利,死则遗其泽。” 【4】齐树楷:《中国名学考略》,四存学会出版部,1923年,第17页。 |